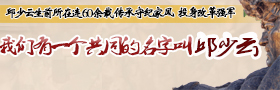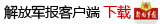要学会骑马只能寄希望于老马了。
在马厩里我抚摸着它的鬃毛,与它脸贴了脸,它大眼睛依恋地看着我,我把马鞍放上了它的背,绕过马肚子扎紧皮带,老马已经很瘦了,马鞍的皮带扣到了最后的扣眼。
我轻轻地踩上马镫,翻身跃上马背。
我真的骑上了它,信马由缰任由它在湿地中游走。它载我去了江滩,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一江秋水、遍山红透的壮美景象,异国往昔黛青色的远山已变换了火红的妆色,草甸依旧碧绿,江水越发湛蓝,加上天上的白云,完全是一幅美妙迷人的画,是一首舒缓动人的诗,是一曲婉转怡人的歌,总之乌苏里江的美让人恍惚。
我从马背上滑落,投入大地的怀抱,躺在沙滩上宁愿长眠不醒,它却用嘴拱醒我,仿佛提醒我还有正事没有做。是的,我骑马出来是去完成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下雪之前积攒足够十匹马吃一冬天的草料,我骑着老马是去找马草茂盛的地方。
我在马背上神游,老马在草甸上漫步,但它却没来由地马失前蹄,我从老马背上跌落,在半空中我还以为是老马前腿被绊了,当我落地时才意识到我掉进沼泽里了,我拼命地扑腾,老马挣扎着从泥潭里拔出两条前腿,它成功了,而我的身子却在下陷。我大声喊救命,我挣扎着去抓马的笼头,却怎么也够不到。我绝望地看着老马,老马定在原地,眼里竟滚落大滴大滴的泪。
让我绝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老马又重新跃入沼泽之中,任由我从它身上爬过。当我爬到岸上,老马挣扎着昂起马头,我看到了它湿漉漉的眼睛——老马流着眼泪,那是对这个世界眷恋的眼泪,它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平静地沉入了泥潭。那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5岁的男人第一次为了一匹马失声痛哭。
老马死的那天晚上,连长把我叫到他宿舍,给我倒了一杯酒,我一饮而尽,高度烧酒的辛辣呛得我眼泪都下来了。
连长说,老马已经超期服役20年了,它比全连所有人都大。我到连队当兵时它就在了,它是咱连队的功臣。没有它,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年,连长还是一连的一名普通战士,他报名考军校那次,正赶上连降大雨,连队通往外面的路断了,电话、电台与外界都联系不上,眼看考试的日子就到了,二百里路,走着去根本不可能。连长的老指导员让他骑马去,于是他骑着枣红马,一路策马扬鞭,老马风驰电掣,6个钟头就赶到团里,老马的鼻孔和嘴角都渗出了血……难怪连长每次到马厩时都无比惆怅,仿佛陷入往事的无限畅怀之中。
老马本该驰骋疆场,奋蹄嘶鸣,去建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但它却在一个边防连队终老一生。
2009年,连队通往外界的公路通车了,连队骑马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那些为连队立下汗马功劳的马被送到了江心的一个鸟岛上自由自在地驰骋。
2012年,我成为一连第24任指导员,某一天,连队组织看电影,放映的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将近3个小时的影片让战士们如痴如醉,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在连队养马的经历。我含着眼泪看完了这部片子,不仅因为电影里那匹叫乔伊的战马,更因为在这片湿地里长眠着我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