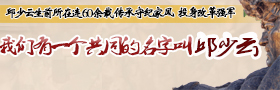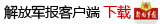最后的军马
孙东亮
2006年秋天,连队最好的一匹军马倒下了。
给老马送行的那天,全连人都去了,在老马长眠的地方,全连兵垂头肃立,连长神色凄切,眼圈通红,他把压满空爆弹的轻机枪举起,向天鸣枪。南飞的雁阵发出一声声悲戚的惊鸣,白色的芦花也在随风颤抖,仿佛抽泣着耸动肩头。五彩秋山作帐,锦绣湿地为床,老马头枕着乌苏里江,永远安眠在了那片土地上。
送别老马,全连战士默不作声地从我身旁走过,没有人看我,没有人理睬我,我从他们的眼中分明读出了无声的愤怒和无言的谴责。
战士们走远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愧疚地伫立在泥沼前,忏悔自己。
老马是我到一连认识的第一个“熟人”。

我从地方大学毕业,参军到了部队,原本以为能留在城里的机关,可谁知,美梦会一下子破碎得如此彻底,我被分到一个偏远的边防连队当排长。
客车只能通到离连队还有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子,再往前走便没了路,只见原始的湿地深处有一个观察哨模样的建筑。行李颇重,通信不便,只得等待连队来接,半晌,远远地看见走过来一匹高大的瘦马和一清瘦的兵。
来人是连队的通信员,他说,排长,连队干部都去演练了,连长派我来接您。
他把我的行李被褥放到了枣红马的背上。
我问他是不是不会骑马,为什么不骑马过来?
他说马太老了,驮不动,其他几匹年轻的都参加演练去了。
我仔细端详着,这是一匹很老的马,屁股上有编号“144”,是烙铁烙上去的。老马非常瘦,骨架高大,后脊背被鞍子磨得光秃秃的,身上的毛掉了不少,通信员没给马戴嚼子,只戴了笼头。
怎么现在的连队还用马呢?
路不好走,汽车经常陷住,所以需要用马,不用说全团就是全军区也没有几个连队有军马。通信员骄傲地说。
通往连队的窄路像一条坝子,两边是一大片荷花泡,被水淹了的塔头只露出了半球形的草顶,就像漂在海面的一个个小小的绿岛。
通信员说前些日子水大,小泡子都连成片了,我们这儿的荷花可出名了,听说为了搞旅游,我们这里很快也要通公路了。
从我一脚踏进连队营区那一刻起,我便再也没有心情欣赏美景了。我负责二排排长工作,二排是后勤排,人少事杂,我要管十几号战士、上百口家丁,我每天领着兵放羊、喂猪、养鹅、赶鸭子、打马草、伺候庄稼、收拾马厩,相比这些我更愿意侍弄马。
白天,骏马在草甸上悠闲地吃草,蓝天下成群的绵羊像洁白的云彩飘在草地上。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象激起了我画画的冲动,但我知道,只要一坐下蚊子就会像洪水一样涌上来。
连队的马总共有8匹,屁股上烙了字的只有老马这一匹,也就是说,这是一匹真正的军马,也是连队最后一匹军马。
“马们”整整忍受了一夏天蚊子小咬的袭扰,每匹马的脖子、脸上、眼角和肚皮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蚊子,我用手拍打马的脸,结果满手心都是马血。老兵告诉我,每匹马一夏天少说也被蚊子喝掉3斤血。
面对蚊子,年轻的马会暴跳如雷地打着响鼻、焦躁地摇摆着脑袋或是在草甸上狂奔,甚至把头浸到水中,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只有老马,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它似乎已经习惯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吃点草。
和年轻的马相比,老马的处境要好一些,白天老马可以待在马厩里,它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独守在空荡的房子。我每天都去看它,抚摸它,给它喂盐,梳理马鬃。我会把马草轧碎添到槽里,还在马厩四周点上四大堆湿蒿草,来驱赶蚊子。老马总是很感激地用舌头舔我的手,耳鬓与我的脸亲昵地厮磨。
我到连队两个月,连马还不曾骑过,后勤排巡逻的机会很少,骑马的次数也就更少,战士巡逻回来的时候,我有好几次试着骑上马背,但每次都是没跑几步我就从马背上被颠下来,那些年轻的马脾气太急,是我难以驾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