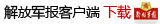周涛近照
诗人周涛今年出版了一本口述自传:《一个人和新疆》。
在书中,我们看到多少有点自恋(诗人总是自恋的)的口述者信马由缰,从自己呱呱坠地一直讲到了著述完成时的66岁,也就是2013年。忽而个人家世,忽而社会实况,多半诚实坦荡,有时不免自视清高、自鸣得意,大致勾勒出了自己的童年印象、青少年成长、上大学、从文从军、逐步获得自己的影响地位全过程,也包括对自己恋爱婚姻的回顾检讨。但这部自述,和我们已知的大部分传记类作品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充分的自我暴露,通过自我暴露也实现了对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和人性事实的还原。看上去,诗人的天性使其摆脱了说谎与文饰,整个文本呈现为一种难得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素材。
大部分的自传都与梦想有关。社会梦,人生梦,追梦的苦痛与创伤记忆,这些似乎能够将一个人从灰暗现实的泥沼中拯救出来,藉此完成“树碑”之意图,或者“盖棺论定”。有的传记写作,甚至宁愿继续把自己藏匿在梦中,以为生命或者是写作的接续,尚可圆梦,这当然都应予以尊重。但有的人早已醒来,不是追回梦的遗失或残破,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真相为镜子,或者标本,映照出社会的痉挛、历史的扭曲,包括对自我本性的暴露。
毫无疑问,周涛正属于后者。
传记显示,自记事起他就饶有兴味地盯着现实,也就是生活本身,也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从个人、家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到名利场。或兴致勃勃,或傲慢心高,或灰心失落,他对现世的倾情关注,使他无从遭受幻灭之痛,结果通篇也就无关乎什么苦难和恩怨。当我把读这本自述的感受讲给一位相交近30年的友人听时,友人击节赞叹:彼所为者,告解也!何种意义上的告解?当然不是基督教那样的人神交通、宽恕祈求,而是在中国一向就有的在“天地”之间的吁请。这是一种真正的中国人的传记:几乎种种的恶都被料到了,苦难的深度也被料到了,但这些都不致让一个人垮掉。只要懂得以最低姿态和身段迎击,知道在必要时降尊纡贵,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落差了。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民族性格中,似乎因外来文明因素而被植入了“天真”的人性观念,即个体生命的纯洁无辜,以及人权之天赋与神圣。岂知在古老中国经验中,“天真”只属于婴儿阶段的人类。不过,也正是这种未经雕饰、没有被浪漫的人文面纱包裹的敞胸露怀,又使这位口述者在某种程度上逼近了西方历史上知名的“忏悔者”卢梭之辈。
周涛1946年出生于山西潞城县马场村八路军总部。请注意,这是一个奇特的摇篮,这种环境里发芽生根的种子前所未有,这一代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直到他们受教育、长大成人的全过程,正是中国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段。而且,恰如周涛这样如今被俗称为“红二代”的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事实上正扮演着“中坚力量”的角色。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们作为“人子”的内核与精神气质,他们的道德情怀,甚至可能事关这个国家的前景。所以,一个像周涛这样的个案的自我呈现,就有了代表意义。从山西——他至今有亲人在那里——到北京,然后在9岁时随父母迁徙到新疆,在那里上学读书,舞文弄墨博取功名,然后预备着要“终老天山”的诗人,看上去是在作自我回顾,实际上也从一个极为特殊的视角,展示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社会生态和人文景观,从文献的、历史的研究中当然也可以抵达,但从个体心灵的层面,特别是从触觉灵敏的诗人口中毫无遮拦地说出时,我们仍不免会遭遇发生认识论意义上的震惊:国家民族的发展之计,理想主义式的群众动员,官民关系、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实质,以及精神资源、信仰渠道的单一匮乏等等,多有出人意表的映现烛照。
父母、家庭的颠覆起落,在他的命运之途中都有鲜明标记。他甚至检讨了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政治考量”——通过出身好、社会地位稳固的家庭关系确保自己地位的安全。作为诗人而如此的讲求实际、如此的不够浪漫,这些可能会让某些文艺青年们错愕。然而,相对于社会历史细密“肌理”的剖露,“人文”的修辞层面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正是具有赤子之怀的诗人才能够做到的。不仅如此,这种源于感性的“在场”的经验,也让我们更贴近地获得了一种关于人性的知识: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现实中,一般人认识的成长建构是如何发生的?在历史理解、历史认知的方式被概念化之前,个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所谓民族性格,或国民的集体性格、集体记忆,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学与生理学前提?这些至关重要。
经由文学之路,周涛的人生确也达致了某种成功。然而在这部自述中只要讲起文学,他都没有什么好气。除了约略得意于早期的荣誉地位,比如全国新诗奖等等,其余就不那么客气了。譬如他发觉,中国“文坛”中的那点水有些浑浊,当代文学的评价标准也是混乱的,国民的艺术审美中掺杂了太多外国趣味,千年文脉和传统却被斩断了。他的羞惭则包括了:由于自己的诗歌渊源与闻捷、贺敬之这样的诗人相关,在“朦胧”“现代”的诗歌修辞烟雾中他败北了。再就是,自己身在新疆几十年,大学里学的是维语专业,却终未能精通维吾尔-伊斯兰文化的深奥和精妙,也就难以在文学表达中有更大作为。
《一个人和新疆》的出版提醒我们:已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立传的“高发期”了。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撰述,或许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些人的诚实、客观之类的品格,但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怎样看待自己的生命经验,有没有勇气进行自我解剖,乃至自省、忏悔,是值得关注的。因为除了“沉默的大多数”,除了内敛羞涩的士人、知识分子类型,活跃于当代中国社会诸多重要领域,并有可能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建构施加深刻影响的,就要数拥有所谓“红色”基因的这个群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