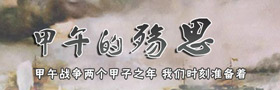和美国一样,俄罗斯很早就筹划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如今俄罗斯的反导武器系统主要由A-135导弹组成,负责防御首都地区免遭核打击。图为正在向发射井装填的A-135。高超声速武器的出现,可能彻底改变导弹攻防作战的面貌。
美国仍是领先者
截至目前,关于中国此次试验披露的信息极少,几位议员据此就作出“中国高超声速武器技术超越美国”的结论显然武断,估计他们自己都未必全信。但信与不信并不重要,能以危言震动政府决策者才是真实目的,你们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虽然美国国防部在发言中隐晦地表示似乎掌握了更多细节,但就目前的现实技术情况看,要细致地监测一次在未知地域未知时间开展的高超声速飞行试验,能测试到大致飞行速度和高度已经十分难得,要掌握更多的细节即便不是Mission Impossible,也极为困难。美国国内一贯有不少防务人士消息甚为灵通,倘若美方真有具体试验细节,想必逃不过这些人士的打探,更逃不过新闻媒体的追逐。
事实显然更具说服力。过去数年间,美国高超声速武器已经进行了多次试验。2010年4月22日,美国洛克希德HTV-2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由“弥诺陶”IV Lite火箭发射升空,开始首次飞行试验,但在试验进行到第9分钟时飞行器出现失稳,弹载安全系统对其实施指令降落坠海;2011年8月10日的第二次试验中,HTV-2再次在飞行到第9分钟时失稳坠海。HTV-2飞行试验失败后,美国国防部预先研究计划局(DARPA)发表声明,认为失败的直接诱因是极高的飞行速度。极高的速度导致的气动载荷和热载荷让机体上的部分蒙皮脱落,在飞行器周围诱发了强烈的脉冲激波,导致飞行器突然滚转,扰动强度超出了HTV-2自行纠正能力。这些异常让飞行安全系统选择让飞行器受控下降,最终溅落海洋。评估认定,第二次飞行中产生的激波扰动,超出了设计承受能力的100倍。“我们正在加深对于高超声速飞行气动控制的理解”,DARPA执行主任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些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未来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空气热力学结构有重要意义。只有实际飞行数据能为我们揭示真相”。虽然试验在“9分钟瓶颈”前频频失利,但HTV-2仍在飞行中实现了20马赫的高超声速飞行,展现出极富潜力的应用前景。
美国另一种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波音X-51“驭波者”高超声速飞行器在2013年5月1日的试验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那次试验中,美国空军从一架B-52H“同温层堡垒”上投放的X-51在60 000英尺(18 288米)高度达到了5.1马赫的飞行速度。这次试验被美国空军称作“持续最长的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也是X-51的第4次试验,也是为期9年耗资3亿美元的项目的最后一次试验。如今X-51项目预算告罄,美国空军正期望后续高超声速飞行器/导弹计划能获批准。美国空军明确表示,他们希望最早能在2015年前后部署无人驾驶的高超声速武器,而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完成高超声速武器的乐观进程将在2020年前后。
基于以上事实,很容易做出更为合理的评判。在高超声速技术方面,美国仍是领先者,美国距离实用化的先进高超声速武器更近,尽管目前还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在如此高的速度下实现精确的飞行控制,这直接关系到武器能否准确命中目标。此外,持续高超声速飞行带来的热量积累也要求人们开发更好的“超级材料”,以便能够耐受高超声速飞行时气动加热产生的可怕高温。
美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都对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展开了研究。美国将这项技术作为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看来,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除关心这一点外,还期望这项技术为突破美国构建的导弹防御系统提供可能。事实上,正如星爷电影《功夫》的经典台词“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极高的速度加上独特的弹道设计,的确让高超声速武器成为导弹防御系统面临的全新严峻挑战。诞生自冷战时代的导弹防御系统的针对目标是传统弹道导弹,而中国此次试验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却是由火箭发射至100千米高度,加速到极高速度后开始俯冲滑翔,依靠控制系统进行机动,飞向预定目标。这种高超声速飞行器并不像弹道导弹那样飞出大气层后弹头再入飞向目标,而是始终保持在大气层内(典型弹道导弹弹道高度一般为150~400千米),这就让原有导弹防御系统对此类目标的探测、跟踪和拦截都出现了困难。特别是拦截器在应对这类高超声速目标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重心分析人士瑞克•费舍尔接受华盛顿自由灯塔网访问时表示,“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HGV)的诱人之处在于它能以高超声速完成精确打击,同时保持较高的飞行高度和低平的弹道,这样导弹防御系统就很难对它作出有效打击”。对于中国国防部对于试验事实的确认,费舍尔认为这一举动“不同寻常”,但却是“积极的表现”,“美国官员对中国军事发展情况说得越多,就越能促使中国军事更加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