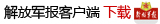只要三中全会涉及军队的改革框架都落到实处,那么文艺队伍大幅度压缩,尤其改变职能定位和建设模式几无悬念,这并不仅仅源于体制编制调整的改革目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时代发展对文艺队伍和文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么,我军的文艺队伍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变化的深层动因是什么?我们该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文艺队伍?笔者在这里谈个人的理解和思考。
为什么我军一直保有一支规模较大的文艺队伍?
我军与西方军队差异很大,其一是文艺队伍建设,这甚至不仅是理念和形式内容上的差异,而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差异。比如,二者的精神力量来源不同,决定了对文艺的需求有差异。
虽然两种制度下的军队都是因政治使命而立,但由于对政治本身的认识不同,政党在军队中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同,导致赋予文艺工作的使命任务不同。西方国家军队本质上秉承政党意志,表现出来的却是国家意志或国家利益;利益就是利益,大多数情况下会让位于道义。我军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虽然根本上是履行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但直接赋予使命任务者是党,作为政治集团的政党,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其力量大小往往决定于其神圣性,也就是能否占领道德的制高点。这就出现了差异,前者不需要谁去张扬自己的利益观,后者却必须要有更适当的人和方式来张扬自己的神圣性,我军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就承担着这样的使命任务。
进一步讲,从精神力量激发的角度看,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军队官兵几乎百分之百拥有宗教信仰,再加上工业革命发端于西方,其官兵有很强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有了这两大精神力量之源,也便不需要至少不依赖文艺活动;没有政治属性和要求,文艺的功能和作用就会偏重于提升官兵的人文修养,丰富军营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这就是美军战时组织文艺明星上战场劳军的动因,也是不需要明星到,只要艳照到即可发挥作用的原因。既然文艺活动没有更多使命任务,也就不需要花大价钱养专业队伍。除此之外,西方军队的职业化和价值观都决定着不养闲人,包括可有可无的人,每个岗位都必须与直接战斗力相联系。至于文艺范畴的军乐团,最初也是直接带来战斗力。比如吹着风笛的乐手是走在队伍最前列,以鼓舞士气。虽然现代战争导致原有功能弱化甚至消失,但由于礼仪功能产生出来,所以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我军的文艺队伍承担的使命任务很重大,真正与理论武装和精神灌注相关联。基于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将宗教视为“麻醉人民的鸦片”,这就决定了我军不会借助宗教来支撑精神大厦;又由于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落后国家发生,这就意味着因工业分工而来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多未形成,不具有支撑精神、规范行为的作用,因此,我军的精神力量只能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的确立需要不断激发和强化,方可产生恒久力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少,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达成目的的文艺活动,就成了必要选择。所以,这也是我军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高度重视文艺队伍建设,并努力发挥其作用的内在原因。
从我军文艺工作发挥的效能看,也支持着文艺队伍的存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国民党俘虏兵就是观看了《白毛女》,而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成为革命战士,黄继光就是通过文艺方式学习董存瑞故事,而做到舍身堵枪眼。更具体的事例,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边境战事不断,当兵仅仅几个月就走上战场的笔者,感知更为深刻。那个时期的中国军队,处在特殊环境:一个是商品经济环境,另一个是艰苦危险的战场环境。有人形容:“山上守卡子,山下数票子”。那个阶段走来的军人,真正感知了何为“笑也凄清,乐也悲怆”。比如战场上牺牲的军人,其获得的抚恤金不如撞死的一头牛的赔偿金,许多烈士亲人因凑不齐路费而无法赴边疆见儿子最后一面。巨大反差导致了政治思想教育失效,而最能给前线官兵带来心灵抚慰和精神激励的,是军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作品,如《十五的月亮》《望星空》《血染的风采》等歌曲,《高山下的花环》《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等文学和电影作品。由于有作用,因而有地位,这是很长时间里文艺队伍受到好评,且有很大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