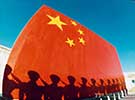我曾经40多次走进西藏。进出西藏的每一条路,我大都走过。有些路走过许多次,但每一次都能有新发现、新感悟;有些路我只走过一次,那也会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最让我难忘的是青藏线、川藏线和新藏线。当兵之初,我就在唐古拉山下修筑青藏公路;川藏线和新藏线我也走过很多次。在西藏,我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一个17岁的新兵,从运兵车上跳下来,脚刚落在高原的冻土地上就晕倒了,再也没有醒来;一个年轻的排长在“老虎口”施工,我刚拍摄完他打风钻的镜头,离开不到几十米,突然发生了大塌方,他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中;一个和我一起从陕西老家入伍走上高原的战友,早上还和我高高兴兴地开玩笑,中午他就连同他的车一起掉进了汹涌的帕龙藏布江……
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想念他们,想念西藏,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西藏。每走一次西藏,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透彻的洗涤和净化。通往西藏的高原路上,每一公里都有一个筑路兵年轻而崇高的灵魂,每一个脚印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时常按捺不住自己,有一种再次行走西藏和向人诉说的欲望。
我写书,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我那些死去的和现在仍然生活战斗在雪域高原的战友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路格桑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这部长篇小说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写成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
从1983年起,我就不断地进藏,几乎每年都要去一两次,最多的一年去了5次。进藏的每条公路都有我战友的身影。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用生命维护着生命之路的畅通。在西藏,我体会最深的是:死去的容易和活着的艰难。内地都市里的人生活在喧嚣和各种欲望之中,而我的战友们在生命禁区不敢有什么奢望,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任务,尽好一个军人应尽的职责,然后,活着回到亲人们的身旁。
在西藏行走的次数多了,忍不住就想写点东西。6年前,我已经写了3部长篇小说和1部散文集,但似乎都没有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完全表达出来。于是就再写,便有了这部《一路格桑花》。这部书起笔于2003年5月,写了6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发现走进了自己固有的模式。我不愿一本书与另一本书相同,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准确地表达出我的思想。一年半后,我偶尔悟到了两句话: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我的心灵为之一震,这不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吗?我一下子抓住了这部书的灵魂。书的基本框架也马上有了:用几个都市女性的视觉去再现西藏筑路军人的工作和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用内地的喧嚣与高原的宁静、都市文明与雪域文化的强烈碰撞,个人情感与神圣职责、家庭冷暖与国家利益的交织抉择,演绎西藏筑路军人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春节长假期间,我足不出户,闭门写作,用了22天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18万字的初稿。“五一”7天长假,我作了一次润色与修改,便交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张鹰。
格桑花生长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山上,又称娑罗,她的故乡是西藏、青海、川西、滇西北那无边的雪山草原,被藏族乡亲视为象征着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也是西藏首府拉萨的市花。她喜爱高原的阳光,也耐得住雪域寂寞与风寒。她美丽而不娇艳,柔弱又不失挺拔。格桑在藏语里就是幸福的意思,所以也叫幸福花。这不正是我们高原官兵的筑路精神吗?格桑花,一种不屈生命的象征,一种崇高精神的象征!
《一路格桑花》是我酝酿时间最长、写作时间最短的一部作品。我对里面所写的内容太熟悉了,里面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有生活原型,有的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有的人物是我非常熟悉的战友。书中的王力,真名叫王立波,他是汽车驾驶员,跟我同年入伍。他死过3次,有两座坟墓。一次是煤气中毒,昏死了3天才被救活;一次是拉运施工物资,被大雪困在了山上,吃草根喝雪水,坚持了5天5夜,最后昏死过去,被战友救出后,在卫生队躺了半个月。最后一次他再也没有活过来。那天早上我结束采访,准备离开他们支队,他到车前为我送行。几个小时后,他去执行运输任务,车子掉进了江里,他和另外两个战友一起牺牲了。十几天后战友们才在下游找到半具尸体,以为是他,就掩埋了。可是第二年春天,战友们在下游几十公里的地方又找到了半具尸体残骸,有人认出上面裹着的毛衣碎片是他的,这才确认是他,又掩埋了一次。所以,他拥有两座坟墓。但是他的爱人怎么也不相信他已经死了,一直盼望他某一天能突然回来。爱人苦苦等了他10年……
写作过程中,我时常忍不住泪流满面,只好停下来,洗把脸再接着写。
我们部队的官兵太苦了,但他们“身在苦中不知苦”,常年默默无闻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我的战友们就像格桑花一样,悄悄地开放在西藏荒芜的大山里,开放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战友们守护着通往天堂的道路,格桑花陪伴着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英灵。
我将书稿交出去几天后,张鹰编辑来电话说,不用修改,马上出版。我放心了,开始做下一件事情:再一次离开北京,走上西藏。
这次进藏,我从新疆叶城沿新藏线而上,翻越10多个冰达坂,穿越了阿里无人区,到达拉萨后又沿川藏线一路而下,经过许多塌方、雪崩、泥石流区域,一直走到四川成都,历时40多天。一路上,我多次遇险,有时甚至感觉走到了死亡的边缘,触摸到了死神的额头。这是我对生命的又一次挑战,也是对自己毅力的一次考验。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活着回来了,尽管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一病一个多月。但我没有倒在西藏,没有倒在采访途中。
一路上,我多次被我的战友们打动。沿途的每一个中队我都住过一两天,我采访了许多官兵,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后来,我将那次经历和多次进藏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再后来,这本书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我说:“通往西藏的路,我走了20多年;通往领奖台的这短短几十米的‘星光大道’,我也走了20多年……鲁迅是一种精神,西藏也是一种精神。鲁迅让人的灵魂觉醒,西藏让人的灵魂净化。感谢西藏给了我灵魂一个栖息的地方,感谢我长眠在西藏和现在仍然战斗在施工一线的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写作的源泉、勇气和力量!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走在西藏的路上,你时常会遇到朝圣的信徒。他们从遥远的地方磕着等身头,一步一步,一直磕到圣地拉萨。他们是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我也是在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我的战友们平凡而崇高的灵魂。
7月19日晚,根据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改编的20集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有一位转业到北京的老战友,他以前是我的老领导,为庆祝《一路格桑花》开播,他设宴招待我。他对我说,昨天晚上看了电视,你嫂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哭了。席间,我们谈的都是西藏和部队的生活。他讲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的细节:有个战友牺牲了,手臂僵硬,他背着他从山坡下往上走,每走一步,战友的手都打一下他的耳朵。说着,他的泪涌了出来。他突然站起来,对我说:“益民,我代表曾经在西藏战斗过的战友,向你敬一个军礼!”他流着泪,给我敬了一个军礼,我也还了他一个军礼。然后,我们相拥而泣……
这就是我的战友们!面对他们,我怎能不心怀感激,眼含热泪?我怎能轻易放下手中的笔?我注定要一辈子为我的战友们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