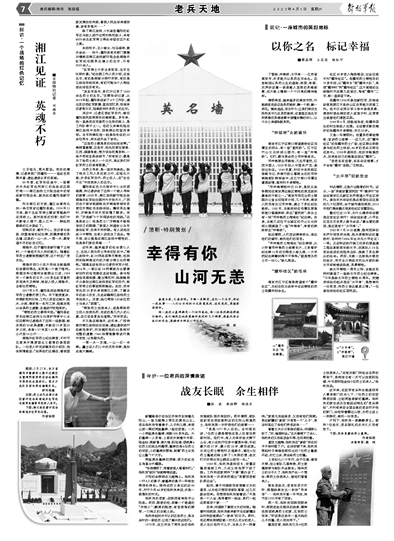春意正浓,又逢清明。手捧一束鲜花,追忆一个名字,讲述一段故事……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祭奠英烈、追思英烈,厚植家国情怀。
每一座烈士墓碑都是一个信仰高地,每一位英烈都值得铭记缅怀。我们撷取各地祭奠缅怀英烈的几个侧影,愿春风捎去我们的思念,愿精神丰碑在心中永驻。
——编 者
探访·一个战场的红色记忆
湘江见证 英魂不朽
■本报特约记者 刘德安
三月桂北,草木葱茏。雨后的清晨,记者来到广西灌阳——一座红色资源丰富、遗址遗迹众多的县城。
89年前,红军长征途中,一场事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血战在这里打响——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的首战新圩阻击战,就发生在灌阳县新圩镇。
作为湘江的支流,灌江由南向北如一条玉带穿过灌阳县城。1934年11月底,数千名红军将士脚穿草鞋奔行在浮桥上。面对敌机的扫射,他们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中……鲜血把碧绿的江水染红了。
回眸历史,感怀于心。走访昔日战场,仰望高耸的纪念碑,抚摸肃穆的英名墙,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道不尽的红色记忆。
酒海井,位于灌阳县新圩镇下立湾村,一个曾经不为人知的地方。随着红军烈士遗骸被挖掘打捞,这个村庄广受关注。
酒海井因口小肚大形似当地盛酒的容器而得名,实则是一个地下暗河。根据史料记载和当地群众口述,1934年一个寒冷的日子,100多名红军重伤员因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投入酒海井,全部壮烈牺牲。
2017年8月,灌阳县启动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打捞工作。井下地质复杂,布满淤泥和石块,工作人员经过抽水、阻水、分流、清淤等一系列工序,陆续发现20余具烈士遗骸,妥善进行收殓保护。
“牺牲的烈士都很年轻。”灌阳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被发现的20余具遗骸,年龄在15岁至25岁之间,身高1.37米至1.63米,体重53公斤至55公斤……
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碑前,不时可见前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参观团队。一位老人听完讲解员的介绍后,饱含深情地说:“如果他们还健在,看到国家发展欣欣向荣,看到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该有多高兴……”
除了湘江战役,3次途经灌阳的红军还与敌人进行过两次殊死战斗,共有6000余名红军将士将生命留在这片红土地。
朱弥陀子、王小曾女、刘马福寿、黄水金生……如今,灌阳县有关部门掌握并镌刻在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英名墙上的名字,只有3500余人。
“红军将士大多出身贫苦,名字也比较朴素。”纪念园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名字,有的是按辈分排行所取,有的是父姓加母姓而来,有的可能与个人特征或生活经历有关。
“其实早些年,我们只记录了1800余名烈士的名字。”吕辉告诉记者,从2014年起,灌阳县组织了6个工作队,通过走访老红军家属、查找回忆录、咨询亲历者等方式,陆续获知许多烈士的名字。
采访中,记者见到红军后代、曾任灌阳县民政局局长的俸顺喜。多年来,他一直奔走在完善烈士名单的路上,是工作队骨干之一。他的父亲俸旺桂在湘江战役中负伤,因被群众收留而幸存。当年和俸旺桂一起参加长征的20余位同乡,却永远失去了音讯。
“这些烈士都是我的伯伯叔叔啊。”俸顺喜感慨,这些年,他先后前往湖南、江西、福建等地,想方设法收集资料,一丝不苟核实具体细节,“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给烈士亲人一个交代,表达我们对红军烈士的崇高敬意。”
为烈士寻亲,是一场双向奔赴。除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努力外,在桂北大地,许多红军后代、烈士后人,在“念念不忘”中找到亲人的名字。
灌阳县红色文化培训中心主任胡海源,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2020年,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对外开放不久,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牙韩高带领学员前往开展红色实践活动。瞻仰英名墙时,牙韩高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突然,“牙美新”3个字闯进他的视线。“这是我叔公!他是烈士!”牙韩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家里人知道叔公当年参加红军,后来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在战斗中牺牲,也有人说他当了逃兵。想不到,叔公竟是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他是我们家的英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爱心人士,也加入到为烈士寻亲的队伍中。“湘江战役中,红34师战至弹尽粮绝,包括师长陈树湘在内的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福建龙岩电视台记者邱学军介绍,2016年,一部以红34师事迹为主要素材创作的电视剧在龙岩拍摄。参与报道电视剧拍摄、播出情况时,她接触到不少参加过湘江战役老红军的后代,被红军将士的事迹深深触动。此后,邱学军先后20多次来到湘江之畔,了解当年的战斗历史,为龙岩籍湘江战役烈士寻找亲人。目前,她已帮助120余位烈士与亲人“团圆”。
“帮助烈士找到亲人,或是帮助烈士后人找到先烈,完成的是几代人的心愿,自己苦些累些也值得。”邱学军说。
不只是在酒海井,近年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对发掘收殓的82具相对完整的遗骸、7465块零散骸骨进行集中安放,以告慰先烈。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矗立在人们心中的无形丰碑,是如此高大巍峨。
铭记·一座城市的英烈地标
以你之名 标记幸福
■薛晶晖 王召尧 练红宁
丁香路、仲铭桥、太平亭……江苏省南京市,许多地方以英烈名字命名。这些被冠以英烈之名的道路、桥梁、亭阁,无声诉说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在大地上镌刻一个个闪亮的精神地标。
清明将至,越来越多的南京市民、外地游客走进这些英烈地标,鞠一个躬,献一束花。慎终追远、思古怀今,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其中几处英烈地标,在重温这些名字所承载的英雄故事中读懂如磐的初心,以今日之幸福告慰英灵。
“仲铭桥”头的缅怀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黄桥社区冯谭庄的西头,有一座“重民桥”。江宁区竹山文化休闲公园内,有一座“仲铭桥”。它们,都与革命烈士邓仲铭有关。
邓仲铭原名邓振询,又名邓重民,江西兴国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1943年夏,时任中共苏皖区委副书记、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邓仲铭随部队转移途中,在江宁禄口冯谭庄遭遇敌情,渡河时不幸牺牲。
“邓仲铭牺牲时仅39岁,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南京周边地区牺牲的我党级别最高的干部之一。”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陆军介绍,几十年来,南京人民没有忘记邓仲铭,建立了多处纪念地标。1981年,当地政府在冯谭庄原高桥渡口修建拱桥,取名“重民桥”,桥头立有一块“邓仲铭烈士殉难处”纪念碑。后来,当地又在位于主城区的竹山文化休闲公园建造了一座“仲铭亭”,亭前的拱桥取名“仲铭桥”。
临近清明,人们走近碑亭桥头,表达他们的缅怀,寄托他们的哀思。
“邓仲铭烈士殉难处”纪念碑旁,从小听着邓仲铭烈士故事长大、义务看护纪念碑15年的古稀老人徐九根,一大早把纪念碑擦拭得干干净净。“就是想为烈士尽一份心。”徐九根说。
“耀华社区”的传承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有个“耀华社区”,为纪念抗日战争中在此牺牲的烈士张耀华而命名。
社区80岁老人陶洪银说,过去这里不叫“耀华社区”。张耀华烈士牺牲后的70多年间,从“耀华乡”到“耀华大队”,再到“耀华村”和“耀华社区”,这片地域的名称随时代发展几经变迁,惟有“耀华”二字,被一直保留下来。
张耀华1938年参加新四军,后被组织派到原江宁县赤山区负责地方武装工作。他不仅在同日军斗争中表现英勇,遇到村里生病的老人或孩子时,还常常出钱替他们请医买药。
1944年4月,因叛徒告密,张耀华居住的村庄被敌人包围。主动要求断后掩护的张耀华不幸牺牲,年仅29岁。
又是一年清明时。设置英烈事迹展板、宣讲烈士故事……这几天,在“耀华社区”的张耀华烈士广场,社区群众积极参与纪念烈士活动,46岁的老兵王刚也在其中。1998年退役后,他自学维修技术,后来给自己的维修店冠名“耀华”。
“老老实实经营,实实在在做事,才不会给‘耀华’丢脸。”王刚说。
“太平亭”前的思念
时近清明,正是外出踏青的时节。近日,一场“异地安置居民回‘甲’健步行”活动在南京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六甲社区举行。参加本次活动的是此前居住在这里的几十位居民,由于城市建设规划,2013年他们集体搬迁到其他社区安置居住。
搬迁已过10年,为什么健步活动要选在老社区举行?活动组织者、六甲社区党总支负责人黄书余说:“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有个‘太平亭’。”
1983年7月14日凌晨,滁河西岸的长芦圩坝突然决堤,洪水席卷附近的葛桥村、沿河村(2006年合并为六甲社区)一带。正在附近执行施工任务的原基建工程兵某部班长杨太平,迅速加入18名官兵组成的抢险突击队,挽救了多名群众的生命。然而,为救一名被洪水卷走的战友,用尽全力将战友托出水面的杨太平却被卷进洪流,英勇牺牲。
杨太平牺牲一周年之际,当地在沿河村建造了一座杨太平烈士纪念碑亭。“今年是杨太平烈士牺牲40周年。把健步活动的起点选在‘太平亭’,是想寄托一份哀思,向烈士表达感恩之情。”一位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说。
守护·一位老兵的深情承诺
战友长眠 余生相伴
■张 政 焦祖卿 陶佳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市东湾镇北阳山,一座戈壁滩上常见的黄色山丘。老兵张秋良带着妻子、儿子和儿媳,来到山坡一隅的两座墓碑、7座坟茔前。一大一小两座黑色墓碑,相距200多米远。大的墓碑一人多高,上面依次刻着牛书君、陆金灿、栗新喜、秦大瑞、阮廷福、胡咸真6位烈士的姓名和籍贯,墓碑后是6位烈士的坟茔;小的墓碑齐腰高,刻着“烈士谷克让之墓”7个大字。
两座黑色墓碑的顶端,硕大的红色五角星分外耀眼。
“快到清明了,带着家里人看看你们。”张秋良“叙旧”似地喃喃说道。
夕阳的余晖洒在戈壁滩上。张秋良一行4人的影子,像墓碑的影子一样被拉得很长很长。陪伴在烈士身边的近40年,对于今年62岁的张秋良来说,亦是一段漫长的时光。
张秋良的老家,在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然而,眼前的他,却像一个地道的“沙湾人”:黝黑的脸庞,有些驼弯的腰背,一口纯正的当地土话。
张秋良起初并不认识这些烈士,是当兵时的一段经历,让他了解并走近他们。
1979年,在兰州当了两年兵的张秋良随部队到沙湾驻防。那年清明,部队组织官兵到驻地附近的北阳山祭奠烈士,张秋良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故事——
“我是1977年入伍的。当时班长讲,7位烈士都是牺牲在我入伍前后那段时间。他们中,有人为保护战友摔下山谷,有人在执行任务中遭遇车祸,年纪最大的27岁,最小的20岁,都没成家。谷克让烈士牺牲时正值寒冬,通往6位烈士墓地的路上积了1米深的雪,战友们只好将谷克让葬在山坡另一处。”
1983年,张秋良退役回乡,安置在镇武装部工作,又在父母张罗下成了婚。工作和成家两件“大事”都办妥了,张秋良有一天却突然提出“我要回老部队那边去”。
起初,妻子何福荣没有理解丈夫的意思,以为他只想回老部队看看,过几天就会回来。没想到张秋良接着说:“不是我一个人去,是带着你一起去,我们一起在那里安个家……”
后来,何福荣了解到丈夫的初衷。随着时间流逝,张秋良愈来愈怀念在新疆当兵时和驻地群众“一家亲”的日子。那时,他还帮扶照顾驻地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老人也认他作干儿子,当亲儿子一样看待。“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有他们照顾。我在新疆的‘爹娘’只有我一个‘儿子’,我当初答应了给他们养老送终……”
看着丈夫日日紧缩的眉头,何福荣心软了,“好,俺跟你去。”见夫妻俩下了决心,张秋良的父母虽说舍不得,也没再拦着。
重回戈壁滩,张秋良在“爹娘”所在的卡子湾村落了户。生活安顿下来,张秋良想起村子离曾经祭扫过的7位烈士墓地不远,农忙之余,常去给烈士扫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交通、通信不便,加之部队几番转隶,烈士家属渐渐与部队失去联系。陪伴烈士的日子久了,张秋良产生一个想法:帮烈士找到亲人,替他们看看亲人。
联系老战友、老首长多方打听,根据线索发出一封封“寻亲信”……张秋良年复一年寻找,终于在1995年有了回音。
那一年,张秋良回陕西探亲时,按照老战友提供的线索,辗转找到胡咸真烈士的家,见到烈士母亲,“听说我这些年一直为她的儿子扫墓,老人泪如雨下。”
截至目前,张秋良已为4位烈士找到亲人。“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我相信总有一天可以找到阮廷福、牛书君和陆金灿3位烈士的亲人。”张秋良说。
近年来,在驻军官兵和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关心下,7位烈士的坟茔得到加固,立起两座崭新的墓碑。张秋良的家也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老兵驿站”,不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兵叩开他的家门,由他带着翻过山坡,为烈士送上一束鲜花,寄托一份哀思。
夕阳下,张秋良一家静静肃立。面向7位战友,老兵敬礼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