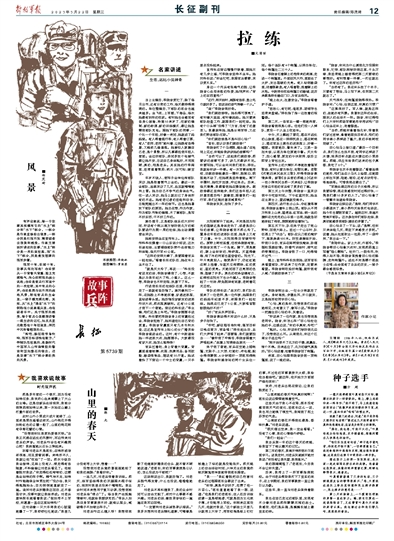一
当上主编后,李晓音更忙了,除了每月出刊,还有日常的工作,每天都排得满满的。单位整编后,下部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坐飞机,上军舰,下海岛,每次她都有别样的收获。有时她也会感觉有些身心疲惫,毕竟50来岁了,但新的编制、新的称谓、新的训练模式,都让她急需到部队充电。跟她下部队的同事,一个比一个年轻,好像一夜间,她就成了妈妈辈。有人帮着提行李,有人帮着订票,有人“老师、老师”地叫着,让她既有些得意,又略添几缕羞涩。她害怕人家嫌自己老,是个累赘,所以凡事都抢到年轻人前面。去边防部队,房间多放个电暖气都让她不安,总说自己身体挺好,不用照顾,真的,咱是老兵。其实她的行李箱里,经常装着胃药、钙片、创可贴、暖宝宝。
年岁不饶人,前阵子去神仙湾部队采访,她是吸着氧气上去的。最近一次去部队,连续采访了几天,血压就噌噌地向上冒。她为自己不争气的身体生气。但一进入采访,她马上就忘记了身体所有的不适。她有老记者的经验和自信,总能挖掘出不一样的细节。这也是她喜欢下部队的原因。她总在想,作为作家,作为部队刊物的编辑,不了解部队,是写不好东西,干不好工作的。
寒冬腊月,正是部队练兵的大好时间,听说有个刚从南方移防到北方的部队要进行为期一周的拉练,她主动请缨前去采访。
她被安排坐在宣传车上。高个子宣传科科长操着一口山东话介绍说,这次长途拉练,主要锻炼部队野外生存能力和体能,每天行军40公里。
“这样的安排太棒了,我要跟着官兵一起拉练。”看着长长的队伍,她在车上坐不住了。
“就是天太冷了,再说……”科长没有说完的话,李晓音猜到了,心想,不就是认为我年纪大了吗,小看人。这么一想,李晓音也不听劝阻,执意下了车。
行进到长长的拉练队伍里,李晓音走了一段就有些后悔了。寒风像利刃一样,在她脸上不停地刮着,穿透迷彩服,直钻进骨头里。她后悔没穿新发的迷彩作训大衣,那衣服真暖和。还有10公里才到下一个营地。旁边的科长说:“李主编,咱们还是上车吧。”李晓音摆摆手说没事。科长要把李晓音身上的背囊抢过去,李晓音拒绝了,她知道他比自己背的更重。李晓音背囊里只有几本书和水壶,这还是宣传车上贴心的女广播员给李晓音装进去的。这时,有个中尉递给她一件迷彩大衣,她摆摆手。大家都没有穿大衣,她怎么能特殊?
官兵扛着枪,身上背着大背囊。背囊里装着被褥、衣服、洗漱用品、备用胶鞋、睡袋等物品,据说有30斤重。她试着拎了下旁边一个中士的背囊,一只手差点没拎起来。
宣传车在旁边慢慢行驶着,跟她只有几步之遥,可李晓音坚持不坐车。她对科长说:“你去忙吧,我跟官兵聊聊,采访更扎实。”
身边一个列兵有张稚气的脸,让李晓音心生母亲般的怜爱,她悄声问:“背上的东西重吗?”
“还行,刚开始时,肩膀有些疼,垫上毛巾就好多了。您说话的语气特像一个人。”
“谁?”李晓音很好奇。
“我们副政委呀。她长得可漂亮了,有时像大姐姐,有时像妈妈。她只要来部队检查工作,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她有个口头禅‘没得了’(方言,没有了的意思)。我最崇拜她,她是女将军呀,又在我们野战部队任职。”
“你们副政委是不是叫田心怡?”
“首长,您认识我们副政委?”
李晓音打了个马虎眼,摇头道:“在电视上见过,你能给我讲讲她的故事吗?”
“当然可以了,说起我们副政委,那要讲的故事可多了,讲几天都讲不完。你要写她,可以去问问我们班长、排长。我就给你讲一件事。有一次军事体能考核,田副政委跑最后一圈时,脸煞白,明显跑不动了,但她硬是坚持着跑。剩下半圈时,她咬牙加速,冲过终点。后来,每天清晨,我都看到她在操场跑步。副政委都还坚持跑步,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好意思落后吗?就像您,跟着我们一起行军,我们还能好意思喊累吗?”
李晓音笑笑,加快了步子。
二
太阳渐渐升了起来。不知是因为阳光的温暖还是身体走热了,或者是田心怡的故事,让李晓音感觉不那么冷了。置身在年轻的迷彩队伍里,她身上又有了力量。中午,太阳照得后背暖呼呼的。原野上树枝虽瘦,但枝条疏朗有致,李晓音发现了一个鸟窝。脚下,草是黄的,踩上去软软的,特舒服。天蓝得像海,结了冰的河面也蓝莹莹的。阳光下,叶片亮黄招人。海棠果干了,仍红红地在树上挂着,与蓝天交相辉映,红的更红,蓝的更亮。天地间因了这亮丽的色泽,温暖了许多。黑色的枝条劲健有力,红柳枝在阳光下也分外媚人。李晓音想起了一句诗: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
带队的排长说:“战友们,我们队伍里来了一位老师,是一位作家,她跟我们的妈妈年纪差不多,却跟我们一起拉练。她现在已走了5公里,大家唱首歌鼓励她好不好?”
“好!”官兵齐声回答。
李晓音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步子加快了。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预备唱!”排长起头后,兵们大声唱了起来:“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像听到了冲锋号,李晓音跟着大声唱起来:“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终于到了营地,官兵在空地上搭帐篷,支架子、上大顶、钉地钉、布电缆,配合得很默契,6分钟搭好一顶班用棉帐篷。李晓音和通信站的两个女兵住一间。每个连队有4个帐篷,以排为单位,每个帐篷住二三十人。
李晓音忍着脚上的泡带来的刺痛,走进一个帐篷里。外面狂风大作,里面生了火炉,发出温暖的光亮。有人钻到睡袋里,闭着眼歇息;有人唱着歌,挑着脚上的水泡。中尉排长收拾帐篷口的睡铺,说历来都是排长睡在门口,为官兵挡风。
“晚上生火,注意安全。”李晓音看着炉子道。
“您放心,有它呢,值班员、团领导也经常来查铺。”排长指了指一边放着的报警器。
第二天,一些官兵一瘸一拐地向前,李晓音看到很是心疼。但他们没一人掉队,更没一个人坐上收容车。
中午,天上飘起了雪花,落在不远处的山脉里,落在一排排民房上,落在树梢上,落在官兵土黄色的迷彩服上,好像一幅画。到营地后,餐车来了。三菜一汤加米饭,以班为单位原地午餐。天太冷了,担心感冒,原定的午休取消,饭后立即背上背包出发。
宣传车上的大喇叭不停地放着强军歌曲,有时以营为单位,拉歌比赛。老歌《打靶归来》《战友之歌》,听得李晓音激情奔涌; 新歌《当兵前的那晚上》《送你一枚小弹壳》《当那一天来临》,让李晓音对身边年轻的官兵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三天上午休整,李晓音一直采访到中午吃饭时间。下午红蓝对抗,她坐在主席台上,望远镜就没离手。
第四天,进行攻占山头、夺红旗等演练,李晓音坐着车上到山顶。部队从不同方向攻上山来,猛虎连、红军连、钢一连的旗帜在光秃秃的山谷里一出现,她就急切地举起了相机,频频地按动着快门。
第五天下午,队伍终于走出了荒山野岭,回到大路上。经过一个山谷时,队伍遇上了“伏击”。部队在尖刀班的掩护下,高速奔袭500米。防空袭演练开始,听到口令后,官兵在路两旁找掩体,卧倒据枪观察敌情。防毒气训练时,烟气忽然喷薄而出。李晓音吸了一口,呛得喘不过气……
晚上,宣传科科长找到她,说军首长来看望部队,听说来了位作家,定要来看望。李晓音刚收拾好帐篷,就听到有人喊:“田副政委来了!”
三
李晓音刚出去,一位女少将就走了过来。身材高挑,步履生风,开口就笑,正是她军校同学田心怡。
“心怡,真的是你,没想到我们在战地相见,太有意义了,像写小说。”李晓音一把握住田心怡的手,笑着说。
“听说来了一位作家,我也没想到是老同学。晓音,你怎么样?”田心怡拉住她的手,边揉边说,“你的手真凉,冷吧?”
“挺好。心怡,听说你们移防到北边了,没想到这么巧。从南到北,你这个江南女子适应吗?”
“刚开始受不了北方的干燥,流鼻血,咳个不停。后来适应了,北方的暖气真是好。”田心怡说着,拉着李晓音回了帐篷。
夜里,田心怡跟李晓音挤到一顶帐篷里,说了一晚的话。
“晓音,你问为什么调到北方没跟你联系,忙呀,部队刚移防到这里,千头万绪,我经常晚上睡前得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想好。有时想着一件事,一打岔就忘了。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当然有了。我在床头放了个本子,只要有了想法,马上写下来,否则第二天就忘了。”
天气很冷,但帐篷里烧得很热。李晓音问:“心怡,住到这里,你真的习惯?”
“这算很好了。军人嘛,就是这样的,战地亦有风景。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跟别人的生活不一样。晓音,你记得咱们上大学时那场军事地形学考试吗?”田心怡坐在床上,抱着膝盖。
“当然,那晚你拿着指北针,带着我们穿过密林,拿着地图找目标点,咱们的同学秦小昂掉进了墓穴,我的手被树枝划破了。”
田心怡马上接口道:“最后一个目标点,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有同学还掉进了水塘,结果目标点就在水塘边的小草房里。那晚,供应车给我们送来的包子真香,我吃了8个。”
李晓音也双手抱着膝说:“看着连绵的地形,咱们坐在小马扎上绘图,在地图上标注平原、陆地、湖泊,还有点状符号、等高线等。可惜我现在都忘了。”
“军旅生涯这样的日子太难得,所以我要珍惜,现在我感觉时间过得好快,一晃我们都50多岁的人了。”田心怡拿了一管擦手油递给李晓音。
李晓音边抹边说:“是呀,咱们同学不少都退休了,秦小昂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她今年也要脱军装了。越到这时,我越不想离开部队。这次参加你们部队拉练,我真切地感受到部队建设的步履了。”
田心怡点了一下头,说:“是啊,但你只来体验几天,常驻下来感受才多呢。”说着,她从包里取出一包药,冲了一袋冲剂,“我出去一下。”
“我陪你去。穿上大衣,外面冷。”李晓音帮田心怡拿大衣时,发现那药盒上写着“稳心颗粒”。拉开门,一股冷风,吹得人站不稳,李晓音紧挽着田心怡的胳膊,走向帐篷外。远处不知是哪个班战士在唱: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
(节选自文清丽长篇小说《从军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