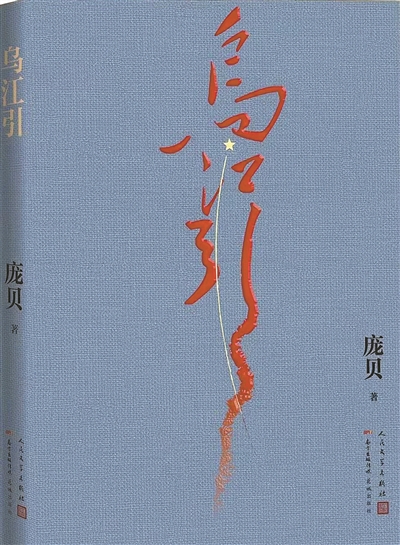从我工作室的窗口向东南方向眺望,不远处就是那个著名历史遗迹的所在。冥冥中的缘分,而今我与那座遗址都处于同一座岛上。近百年前的那个秋日,长篇小说《乌江引》(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2年2月)中主人公的原型人物,那位名叫曾希圣的年轻人,他和其兄长就是一路南下来到这个长洲岛,来到这所黄埔军校。岂料后来风云突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及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被迫转移,黄埔四期的曾希圣已是中革军委二局局长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走夜路”,好在这支“夜行军”有照明引路的“灯笼”,这便是中革军委二局的破译情报。二局随时都要回答党中央和军委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敌人在哪里?
回望那段遥远的历史,有时恍若有某种梦幻之感。梦幻中的夜行军,他们一次次绝处逢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走向黎明。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人类意志和智慧的胜利。那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些“特殊中的特殊”——军委二局的破译者,长征途中他们几乎破译了敌军所有情报,而敌军对于红军的情报却是一无所获。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特例。
关于80多年前的那场长征,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诸如此类的故事几乎已是尽人皆知,此乃一部宏大史诗的相关章节。《乌江引》所要呈现的是这部宏大史诗的“副歌”,是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传奇。长征密电全新解密,由此为人们解开长征史诗的另一个“密码”。这部“副歌”的主角其实只有军委二局的三个人:局长曾希圣、破译科科长曹祥仁、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毛泽东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长征密码情报战,这是一场“无形之战”。作为小说创作者,有了二局的大量解密文献,如何以文学的形式呈现那样一段秘史,此亦是一个考验我想象力的大难题。
《乌江引》是基于准确可考的史实而创作,这个题材给予我想象和虚构的空间其实是很小的。如果做成纪实类的非虚构体裁作品,倒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然而我决意要将这个题材做成具有文学纯度的长篇小说,一部在叙事形式上具有独特结构、视角、语感和节奏的小说文本,一个独具美学特质的“高级文本”。
所谓“高级文本”,必然要具有很讲究的叙事策略。譬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谈论其叙事之美。就叙事技巧而言,这部作品其实是比我们很多纪实类作品讲究得多,这也是我所欣赏的“高级文本”。
斯诺将陕北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喻作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令人昏昏欲睡的长句。很多年前,我也曾在军校图书馆里抱着一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文原著,昏昏欲睡地啃了很多日子。那时我也有幸读到了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英文原著,我至今依然认为赛珍珠也是为我们所低估的一个作家。《大地》写的是我们中国这片大地,而《乌江引》的故事也有“土地革命”这个大背景。母校的那座图书馆,给了我一个世界文学的大视野。小说风格固然可有很多种,但我更爱具有形式美感的作品。要为独特的内容找到一个独特的形式,甚至是最佳形式。在我看来,一部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也理应具有形式的美感。
对于小说形式美感的注重,对于这种小说艺术现代性的感知,始于我多年的文学修炼,我有能力以小说的形式呈现这个传奇,有能力在纯粹的史实和虚构的想象之间建构一种新文体。那些传奇中的人物,他们也到了被更多人知晓的时候了。
于是就有了这部《乌江引》。我希望这是一个“高级文本”。就作品形式而言,我甚至也着力为《乌江引》营造一种整体结构上的节奏感。为此,我严格限定第一部《速写》约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第二部《侧影》约占四分之一。就叙事视角而言,我严格限定人物活动的“景深”:前景是曾、曹、邹这“破译三杰”,后景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后者是以前者的视角出现。又如在叙事语言方面,我力求还原当时的语境。譬如,在海量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那时很多人在量词的使用上并非总用“个”字,他们不说“这个土豪”,而是说“这只土豪”。又如,彼时各级指战员他们在口语中并非是喊“政委”,而是“政治委员”。即令是在万万火急的危情时刻,他们也不用这简称。诸如此类的修辞细节,都是构成一个高品质文本的必要元素。我深知即便是处理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语言也依然应是小说品质的第一元素。
这是一次高难度的创作。党和军队领袖人物的出现,对于作者来说,就不只是要遵从一个“大事不虚”的一般原则,这里所有的细节必须言之有据。我试图以独特的构思解决这个难题,最终文本所呈现的这种“亦文亦史,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正是一种创新性叙事文本的质感。在这个独特的结构形式中,第一部《速写》与第二部《侧影》形成一种独特的复调叙事,这也是某种对位和同构,而《速写》中对“我们”这个给读者以代入感的人称使用,《侧影》为扩展更大历史时空所用的“缠绕式叙事”,亦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原创性。
《乌江引》固然是长征史诗的一种解密,固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史学界和文学界已有评价说,这是“对伟大长征精神的崭新书写”,而我也要呈现人在身心极限状态所迸发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生命力的“超常实验”。
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不为人知。无尽的时光深处,依然有他们青春的身影。这也是一个关于寻找、关于记忆与身份的故事。我们党和军队的创始人,以及军委二局的领导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以现代形式的长篇小说呈现这种史诗,在主题上我也力求有多维度的表达,以使作品有更为丰富的意蕴。比如,“人类记忆”亦是一个隐含的主题。那些破译者无疑都是记忆力超群的人,但工作性质要求他们要及时清除某些记忆信息,甚至会因用脑过度而失忆。而在这个作品的另一个时空,今人执着寻访、打捞记忆的碎片,诸如此类的描写,共同构成这个有关记忆的主题。
拒绝遗忘,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历史洪流中的个体生命,我们理应予以敬重。即便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尘封的侧影,也足可给予后来者以行动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