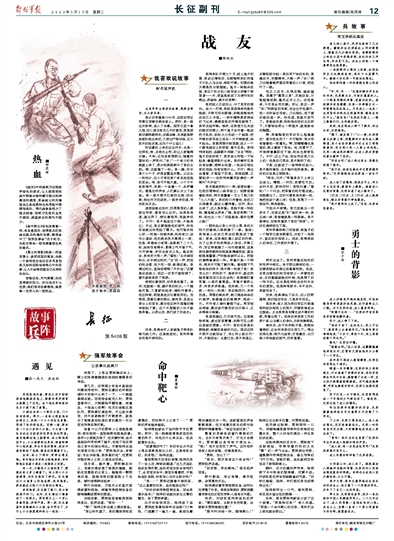一
这是爷爷生前讲的故事,现原话照录,与大家共享:
我认识李嵩是1943年,在胶东军区军事五项赛的刺杀场上。那时,我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决赛。冠军已经十拿九稳,但心里总有点儿不好意思:我是团部侦察排副排长,侦察兵嘛,本来就是野战部队挑出来的,又受过严格训练,五大技术的起点高,还比个什么劲儿!
听说最后上来的这名对手,也是一位排长,咳,点到为止吧,别让人家输得太惨。不料,还没容我想明白,随着炸雷似的一声吼叫:“杀!”一个有力的突刺就上来了,那木枪狠狠刺中了我的左肋。得,这就输了一枪。我一瞧,对手是个小个子,护具穿戴蛮齐整。从这头一枪估计,这小子肯定是个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唔,我可不能大意。小个子不容我喘气,突刺一个连着一个,杀声震天。要是光听声音,人们真以为上了战场。我一面不慌不忙地防左刺、防右刺,挡住对方的进攻,一面步步后退,寻找机会反击。
退到场地边沿时,四周围观的人都屏住呼吸,看我怎么应对。如果我再退,就出界了,按比赛规则,我就弃权了。不行!我不能丢这个脸,不能再让!不过,我还要挫挫他的锐气,和他沿场地边沿兜起了圈子。他可能求胜心切,一枪接一枪地突刺,枪枪有力,说句公道话,他的刺杀技术算得上一流,但是,毕竟体力有限,连续刺了二十几枪,始终没有得手,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步伐也有点儿乱。趁此机会,我突然大吼一声:“看枪!”左手缩回枪尖,右手顺过枪托,“当”的一声,把他的枪击落,他大吃一惊,跌倒在地。我调过枪尖,直指他咽喉:“不许动!”这要是在战场上,他这一百多斤就报销了,要不就被我抓了俘虏。
按照比赛规则,自然是他输了。谁知,他就地一滚,避开我的枪尖,一个鲤鱼打挺,又重新站起来,端枪对着我。他这样做,明显是违反比赛规则的。没想到,观看比赛的群众、裁判员、甚至主席台上的首长,都为他这种不服输的精神鼓起了掌。这个不服输的小伙子就是李嵩。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好战友。
二
后来,我奉命打入县城鬼子特务队做内线工作。这是绝密的。我和李嵩自然是不辞而别。
到特务队不满三个月,赶上鬼子扫荡,我送出情报后,也跟随特务队和鬼子大队人马出动,相机行事。扫荡的地方都是抗日根据地。鬼子一路烧杀抢掠,我这个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却像个旁观者——不,简直是变成了为虎作伥的帮凶,那滋味,真不好受啊!
我把敌人引进后山,中了我军的埋伏。战斗一打响,我赶紧选择有利地形隐蔽,子弹可没长眼睛,别糊里糊涂死在自己人手里。一排手榴弹黑老鸦似的飞过来,滴滴答答的冲锋号就响了,我军发起冲锋。倏然,在我前方五米远的梯田田埂上,两个鬼子兵守着一挺歪把子机枪,机枪火力扫成一个扇面,把冲锋的我军战士压在一片开阔地里,抬不起头。我朝周围仔细观察,敌人一个个都龟缩在土坎背面,看不见我。我悄悄举起枪,连瞄都不用瞄,“当当”两枪,鬼子的机枪哑了,我军战士呼啦一下站起身,像猛虎般扑过来。我好像听见身后有动静,便转头张望,一块岩石挡住我的视线,没有发现什么。不行!得过去看看,不能留下后患。我猫起腰,正要起步——忽然传来震耳欲聋的一声喊叫“不许动”!
我本能地把枪口一转,面前站着一位怒目圆睁的八路军战士!他腰里插着驳壳枪,两手紧攥着一支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我的枪口对着他,他的刀尖指着我,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我认出来了,这人是李嵩。我脑子里一阵松弛,嘴里喊出声来:“哦,是老李啊!”不料,他吐出一句:“无耻叛徒,看你往哪儿跑!”
一腔热血从我心中往上涌,我的太阳穴好像被人狠狠揍了一拳。叛徒!我陈某人在自己同志的眼里成了叛徒!原来,在我离队潜入敌区的时候,为了让我尽快取得敌人信任,开展工作,军区特地搞了一份内部通报,说某团侦察排副排长陈某某携械投敌,望各部提高警惕,严防叛徒破坏云云。把假的演得像真的一样。李嵩只是一个排长,根本不可能了解内情。看他眼下气势汹汹的样子,恨不得一枪挑了我!我怎么办?把枪扔下,高举双手,就这样随李嵩回自己队伍去吗?我眼睛盯着李嵩,心里打着算盘。李嵩不管那么多,向我步步紧逼。他突刺,又一个突刺,一枪比一枪狠!我东躲西闪,步步后退。周围的喊杀声,刺刀捅进肉体的扑哧声,铁器撞击的铿锵声,响成一片。不时有人惨叫着倒下去。两军短兵相接,都在进行激烈的白刃格斗,正杀得难分难解。
我退到崖边,已无路可走。这里地势较高,透过层层雾霭,依稀可见山那边县城的剪影。不行!我的任务是长期隐蔽,做解放县城的内应。现在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了,怎么向上级交代?对,不能回去!主意已定,我不再退让,右脚轻轻勾起一具伪军尸体的长枪,紧握在手,抖擞精神,大喊一声:“杀!”刺刀尖随着喊声落在李嵩的心口窝,把他吓了一跳。
他正义在手,仇恨在胸,越战越勇。我属于“戴罪之身”,无地自容,只能勉强招架,毫无还手之力。在他看来,今天我必死无疑。所以,我这一声“杀!”和狠劲的突刺,完全出乎他意外,他一点防备也没有。刀尖指处,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你后退,我就不客气了。我接连突刺,枪枪指在他的左右肋下,只要移动那么一两厘米,就是致命的胸膛。
啊,李嵩胸前的军衣怎么湿漉漉的?莫非他负伤了?不可能呀,我并没有碰着他一根毫毛。啊,军帽帽檐也是湿的,脸上像抹了层油。他,他冒汗了,汗珠顺着鼻梁往下淌,枪法也渐渐乱了。不行,这么下去,他会死在我刀尖上的!他是自己同志,我不能伤了他!
于是,这就成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不能伤害他,也不能叫他伤害我。最好的办法是立刻脱身。
“排长,闪开!”李嵩身后又上来三名战士。糟糕,一对四,我要吃亏的。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吼叫着:“看枪!”一个闪击,把李嵩的枪打落在地。他脸都白了。这时只要我再突刺一枪,准把他穿个透心凉!但是,我晃了一个假动作,转身就跑。
可他并不领情。我已经跑出一百多米了,后面还是“叭”地打来一枪,我左肩一麻,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痛。我不敢停住,怕被李嵩抓了我的“俘虏”。只好忍痛顺坡往下滚。
我和李嵩拼刺刀的场面,被鬼子的一个随军记者亲眼看见,并拍了一张照片,登在敌伪报纸上。因此,我得到敌人的信任,工作更好开展了。
三
两年过去了。我和李嵩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相见。终于明白真相的他,一定要我脱去衣服让他看看伤疤。他说,在我击落他的枪没有跃上一步要他的命,反而撒腿就跑的时刻,他是愣了好一阵子的。这也是他举枪击发时手发抖的原因。他是特等射手,手不发抖,我就没命了。
后来,他奉调去了东北,归入四野建制,我仍留在华东,又是多年没见。
再后来,有人因为那份军区内部通报和敌伪报纸上的照片,怀疑我曾经当过叛徒。正当我浑身长嘴也说不清的时候,李嵩出现了。他亲自来到我工作的那个省,以当事人的身份,为我洗清冤屈。
离休后,在干休所院子里,我俩拄着拐杖,还会你来我往比划几下。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化战争,打到最后,白刃格斗所练就的胆气,仍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