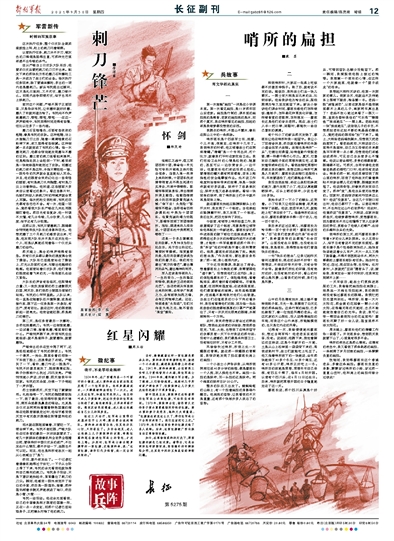一
第一次接触“扁担”一词是在小学课本里。第一次看见扁担,是11岁那年回山东老家。扁担是竹制的,课本里的扁担挑的是粮食,老家的扁担挑的是水,而那个夏天,我在哨所看见的扁担,担起的却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东西。
我蹲点的哨所,不显山不露水,像长在深山之中的一条筋脉。
哨所班长是个四级军士长,姓廖,个儿不高,很敦实,在哨所十几年了。我到哨所的时候,他正领着战士们在洞库清罐。“清罐”是一个专用名词,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平时在家收拾卫生。我们收拾卫生时的心情是松弛的、随意的,甚至可以一边欣赏音乐,一边干活。但廖班长他们却远没那么轻松。要清理的罐大都有两层楼高,须系上拇指粗的安全绳攀援作业。先不说工作难度和油漆味带来的眩晕,单是一块抹布就有好多说道。抹布干了容易扬灰尘,抹布太湿又容易生铁锈。看似一块简单的抹布,到了哨所战士们手中就不再是简单之物。
就在廖班长抬起左胳膊抹额头上的汗水时,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当他扬起右胳膊擦汗时,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我忍住笑,把目光移向了别处。
午饭前,有领导上哨所检查工作,我故意揭穿了这个秘密,用意是想让领导给他再配发一件新迷彩。廖班长穿的那件迷彩服的腋下部位已经拔丝透亮了,那得经过多少次的抬臂动作或汗水的浸渍,才能使一件军装磨损成那个样子!我“拆穿”他的时候是怀着心疼和赞赏的。结果,廖班长却因此挨了批。挨批的理由是,“作为班长,要注意自身形象!”那一刻,我心里很内疚。
下午还没到操课,我就出了宿舍。想着廖班长上午挨批的事,我需要跟他“道个歉”。没想到他们正在列队,身上的保险绳都系好了。保险绳很粗,看着挺结实,都打着好看的蝴蝶结。尽管是盛夏,但因洞库温度低,在迷彩服里面,他们都套着绒衣绒裤。体形虽略显臃肿,但丝毫不影响我对他们心生敬意。当战士们在值班员的口令下向右看齐时,我没有看清他们的脸,因为每一张生机勃勃的脸庞都被厚厚的口罩严严地罩住了,只有一双双无比明亮的眼睛,齐刷刷转向一个方向。
此时,我突然想到以前去过的野战部队,想到生龙活虎的训练场,想到那些坦克、飞机、火炮,也想到了在哨所留守的炊事员前一天下午对我说的那句话:没有什么遗憾的,我们都是共和国卫士,没有岗位好坏,只有分工不同。
风徐徐吹过哨所,所到之处一片耀眼的青翠。就在那一排耀眼的青翠里,我惊讶地发现了担在廖班长肩上的扁担!
一个小战士小声告诉我,从哨所到洞库往返40多分钟的路程,都是廖班长一个人挑,别人换他也不肯。扁担一头担的是抹布,另一头担的还是抹布。两个桶里的抹布总计20公斤。
整齐的队伍又出发了。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有一个担着扁担的身影格外醒目。他肩挑的姿势,让我看到的不只是重量,还有那个快被许多人淡忘了的姿势。
二
刚到哨所时,大家在一张桌上吃饭都不好意思伸筷子。熟了后,就有说不完的话。晚饭后,我和战士们坐一块儿聊天。一期士官大刚是东北来的兵,比较活跃。他给我讲他为啥当的兵,服役期满为啥又坚定地留下来。新兵小徐讲他们课余时间,廖班长教他们怎样做饭、缝被子,怎样栽花种草美化环境,怎样堵食堂的老鼠洞,怎样理发……廖班长还是他们的音乐老师。现在,战士们人手一把口琴,闲暇时,都能吹一曲自己喜欢的调调。
有个叫小丁的新兵那天发烧了,廖班长让他在哨所和我一起留守。我让小丁回宿舍休息,然后就沿着哨所的羊肠小道去找军犬战韬。战韬也是哨所“一兵”,它健壮而勇猛,站哨值勤外带捉老鼠,哪一样都干得尽心尽力。夏天,它喜欢自己摘院子里的草莓和黄瓜吃,还喜欢嗑带咸味的瓜子。看到战韬吃草莓时那副忘我的模样,我想这深山哨所可真是人杰地灵!廖班长说战韬已经服役6年,年底要退役了,他们都挺舍不得。
我没找到战韬,却在山泉汩汩奔流的地方,意外发现了小丁,他正认真地翻晒抹布。石头上晒的抹布,少说也有200多块。
我抬手试了一下小丁的额头,还烫着。小丁怕我又让他回去躺着,机灵地转移了话题。他说,您若早来几天,就能赶上吃“幸运饺子”了。每逢哨所的兵过生日,廖班长都要亲手擀一百个皮儿,包一百个饺子。
我后来求证过这事儿,问廖班长为啥非擀一百个饺子皮呢?廖班长说没啥,“百”在我们老家那边代表“长命百岁”,我希望我带的兵都能“长命百岁”。山里没有生日蛋糕,也没有生日蜡烛,我是班长,我得想法给他们营造快乐的理由。
一句“快乐的理由”,让我记起昨天曾问过廖班长,现在的兵好不好带?他想想说,不存在好带不好带,只有会带不会带。就像我们所处的环境,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看山的时候山是风景,山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风景。
三
山中的月色清凉如水,晚上睡不着转到院子里,月光一角,我摸到了白天见到的那条扁担。这条竹制的扁担,已多处皴裂了,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兵。在这沉寂的大山深处,没人说得清扁担的年轮,而我这个山外来客,所能触摸到的,也只是它内在的风骨。
记得有一天,我曾傻傻地问廖班长,想过当将军吗?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说话间,他蹲下来,拨拉着脚边的豆秧说,这是今年新开的一片地,土是从山上松林里一袋袋背下来的,等到成熟时节,战士们就能吃上毛豆了。他又指着哨所坡下的一块地说,去年那块地结了40多个冬瓜、50多个南瓜,还有60多公斤葱,哨所正好吃上一冬。哨所后的坡地是草莓,草莓年年自己串根,有四五千棵了,每年6月初开园。以前有个四川兵,在6月12日过生日。后来,哨所就把草莓开园的日子隆重地定在了这一天。
廖班长说,那个四川兵真是个好兵,可惜因留队名额少没能留下。那一瞬间,我捕捉到他脸上掠过的惋惜。我理解一个班长的心情,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他就像一个“望子成龙”的母亲。
我想起大刚昨天讲的,他第一次探家的事儿。到家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系上围裙下厨房,准备露一手。老妈一脸“诚惶诚恐”,以前在家是饭不盛到碗里都不上桌的儿子,离家两年真出息了?老妈不放心地过来看了一眼又一眼,直到色香味俱佳的“可乐鸡”“糖醋鱼”“拔丝地瓜”一一摆上桌。老妈夹起一块“拔丝地瓜”,说尝尝儿子的手艺,不想那扯老长还扯不断的亮晶晶的糖丝儿,竟把老妈的眼泪给“扯”下来了。晚上,大刚给老妈端洗脚水,没想到又把老妈惹哭了。看老妈流泪,大刚说自己心里特不是滋味,自己为父母做的本来都是平平常常一点小事,没想到他们却感动成那样,可见自己当兵前多么不懂事。他说以前去酒吧,多贵的酒都敢要,眼睛都不眨。可那天,当同学请他走到曾经熟悉的酒吧门口时,他却没有走进去。转身的那一刻,他的思绪回到了深山里的哨所,回到了他和战友们拿着津贴不知该去哪儿花的情景,眼睛就突然湿了。他说很奇怪,好像突然发觉自己变了。那种“变”,是他当兵前无法想象的。回家时,老妈惊讶地问咋回来这么早?他说“没意思”。当这几个字脱口而出时,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以前在哨所时,不也向往过山外的世界吗?而此时,他竟然说“没意思”。大刚说,在家休假那些天,他做梦都想哨所,更想廖班长,因为廖班长不光让他懂得了军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更教会了他做人的尊严、生活的乐趣和当兵的光荣。
到哨所的第三天,赶巧廖班长妻子带着4岁的女儿来队探亲。女人见到女人,似乎总有着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廖班长妻子是个性格极爽快的人,她快言快语地说着女儿早产,不大一点儿又得了肠套叠,不得不到医院动手术,两次大事都赶上廖班长部队有任务。她当时也哭过、怨过,现在回头想,也没啥。处对象时,人家就把“丑话”撂前头了,说,嫁给我,我肯定会一辈子对你好,但我肯定照顾不上家……
一天早饭后,趁战士们更换迷彩服的工夫,我偷偷把扁担担在肩膀上,结果连一只桶也没担起来,我的狼狈相没有躲过廖班长的眼睛。我慌忙把目光望向别处。哨所旁,长着一大片太阳花,那金黄的花冠像一颗小小的太阳,在浩瀚无垠的天地间,忠贞不渝地绽放着自己的光华。我说,我可以带一棵回去栽到阳台的花盆里吗?廖班长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温室里养不活太阳花。
周末晚上,廖班长他们的清罐工作告一段落了。开完班务会,想到明天我就要下山了,心里竟有很多不舍。
哨所的夜色还是那么清凉。在清凉的夜色中,我又看到了那条熟悉的扁担,一条刻满了岁月凹痕的扁担,一条默默负重的扁担。
恍惚间,我觉得廖班长这个普通老兵,多像这条扁担。廖班长负重的身影,默默穿过哨所的小路,穿过那一重重山峦时,他和肩上的扁担何曾分过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