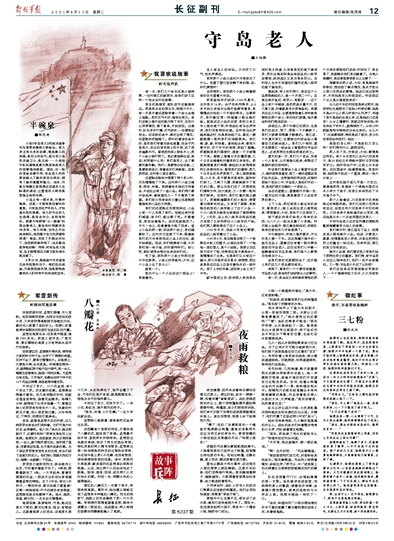有一次,我们几个战友在某小城相聚,一位叫春江的新朋友,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他当兵时的故事:
我当的是海军,部队驻守在渤海湾边。那是我当兵的第五年,刚提干不久,有一天我开着巡逻艇带着一个战士去海上值勤。那天天气不好,海浪也很大。我们在离公海不远的地方转了半天,见没什么异常情况,看了看表,开始返回。出海时,队长多次叮嘱,天气恶劣,一定要保证安全。在返航的途中,真的出现了情况,巡逻艇突然抛锚了。那时的通信设备不好,虽然我们带着无线电装置,但由于风急浪大,发出的信号岸上收不到,试了很多遍都不行。看到老和岸上联系不上,那个小战士被吓哭了。我还算稳得住劲,我说,你哭管什么用!我们是军人,出了事要沉着冷静。咱们一是要想办法自救,二是要保存体力,等着战友们来救援。说是那样说,当时我心里也害怕。
巡逻艇在海浪中漂荡了两个多小时,天色慢慢暗了下来。这时那个小战士喊我:排长,你看。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小岛。我们两个都兴奋起来,像绝望的人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我们努力用身体的力量让巡逻艇顺着海浪向小岛的方向漂。
我们的巡逻艇还没漂到岸边,小岛上有一个人发现了我们。他跑过来对我们喊道:孩子们,船出事了吧。不要着急,我回去拿绳子。说完他就跑走了。不大一会儿,他拿着绳子跑了回来。登上小岛的那一刻,别说那个战士,我的腿都软了。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跟着救我们的大爷来到他在小岛上的住处,就开始做饭。他说,你们俩真有口福,今天我钓到一条大鱼,好好款待你们。放心吧,部队领导会想办法来找你们的。
吃了饭,我和那个小战士听那位老大爷拉家常。小战士好奇地问:大爷,这个小岛上住了多少人?
就我一个。
您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个孤岛上?我接着问。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大爷叹了口气,拉长声调说。
我和那个小战士追问大爷到底为了什么。他望了望已经安静下来的海,说:你们真想听?
当然想听。我和那个小战士睁着探询的目光望着大爷说。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1940年夏天,当时我才16岁。由于母亲死得早,从8岁开始父亲每次出海打鱼都带着我,我慢慢成为他的一个不错的帮手。出事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摇着小船出海打鱼。就是在这小岛的东面,我和父亲正专心致志地下网,听到远处有马达声传来,我们没有特别在意。当听到马达声越来越近时,先是我抬起了头,看见一艘舰艇箭一般向我们的渔船驶来。我忙喊:爹,爹,你快看。爹抬起头来,看到大事不好,扔下手中的渔网,抓起了摇橹。那舰艇到我们跟前时,速度一下子减慢了下来。舰艇上插着日本的膏药旗,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对着我和父亲浪笑。那舰艇围着我们转圈,掀起的水波晃得我和父亲前仰后合,看到我们的窘相,那几个日本兵的笑声更响了。我心里狠狠地骂:小日本,老子要是手里有枪,就和你们拼了。又转了几圈,那舰艇驶开了我们的小船。原以为他们走了,没想到他们调转方向,加大速度,又一次箭一般向我们射来。发现时,我们已毫无能力避让了。那舰艇撞翻我们的小船后,便冒着白烟扬长而去。父亲没了踪影,我被随后赶到的八路军救上了这个小岛,一个小八路军为救我也被卷进了漩涡牺牲了。3天后,岛上的八路军在很远的地方找到了父亲和那位小八路军的尸体。他们两人都被埋在了这个小岛上。
1942年冬天,因战斗形势的需要,驻岛的八路军撤出了小岛。
1945年8月,我在海里发现了一个被绑在木板上的筐子,从里边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是个小姑娘。我原以为这孩子活不了啦,没想到这孩子真是命大,竟慢慢活了过来。也是我们父女有这个缘分,那几年虽然苦点累点,细想想,那应该是我在这岛上这些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到了上学的年龄,送回岸上去上完了中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派人来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父亲是我党的地下通信员,那次出海实际是去给驻岛的八路军送情报,政府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当时敌人也并不知道他们撞死的是八路军的地下通信员。
算起来,带上你们两个,我在这个小岛周围救起的人,差一个不到二十个。这里边有打鱼的、有军人、有船员……这个岛上有个半碗泉,虽然那泉水量不大,但又清又甜,好像就是专为我准备的。我要求在这儿守岛,主要是想陪着父亲和救我牺牲的那个战士,我怕他们寂寞,每天都去和他们俩说说话……
讲到这儿,那个叫春江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战友,哭了,周围一下子静极了。我们大家都觉得鼻子酸酸的。春江说,今年夏天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去岛上看看自己的救命恩人。我们几个相约,夏天也跟春江一起去岛上看望那位守岛的老人,还有那两位长眠在那里的烈士。
夏天的某一天,我们几个老兵,没有一个人食言,从天南海北赶来,相聚在了某海防团的招待所。
听说我们是要去小岛上看望守岛老人,海防团很是重视,派了一艘巡逻舰送我们去无名岛。负责接待的同志说,在海防团每个官兵心中,守岛老人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他们团不在编的一个老战士。
坐在巡逻舰上,望着舱外天海一色、一望无边的大海,真是感到了人在自然界的渺小。
上了小岛,那位被老人救过命的战友,看到老人,跑上去抱住老人痛哭起来,哽咽着说:大伯,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卸下部队和我们给老人带来的东西,七八个人一起足足搬了十多趟。昨天晚上去超市,春江像抢购似的,把部队派来的面包车几乎给装满了。
中午做饭时,所有人强烈要求,不允许老人插一下手。在这浩瀚大海中的一座无名岛上,望着这位有着一脸古铜色面容的守岛老人,这位在我们心中像一座雕像似的无名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想为他做点什么。
送我们来的巡逻舰回去了,这天晚上我们这几个老兵都没有走。
夜深了,看我们一个个都没有睡意,守岛老人说,我给你们讲讲我女儿的事吧:
有一天,我坐在父亲和救我牺牲的那个兄弟坟前陪他们说话,时间长了,我也累了,我就躺在他们身边睡着了。当被人推醒时,我在梦里梦到我女儿出事了……
推醒我的那人说,大伯,我是海城市侨联的,想找您了解点情况,是关于您女儿贺小花同志的事情。她说已找过您两次,不知她是怎么和您说的。听说您这个女儿是从海里捡来的?
女儿在不长的时间里是来过两次,她吞吞吐吐地探问了些她小时候的事,她是不是从什么人那儿听到什么风声了,知道了我不是她的生身父亲,还是她自己的身世?从女儿懂事时,我就这样告诉她,你母亲生下你不久,就得病死了。从你小时候就是咱爷俩相依为命过来的。女儿大了,比谁都孝顺,特别是成了家后,多少次劝我回去和他们一起住……
是捡的怎么样?不是捡的又怎么样?你们想问什么,就明说吧。
那人笑了笑,对我说:大伯,事情是这样的。有个日本老妇人名叫川田美幸子,是20世纪日本侵略中国时日军的随军护士。她怀孕生产时,正赶上日本战败。在归国途中,她遭遇海难。危急时刻,她把孩子放在一个筐里,绑在一块大木板上……
这时我的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要真是那样,我竟给一个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养大了孩子,而我父亲却死在了日本鬼子手下。
那个人接着说,川田美幸子后来被路过的商船所救。我们已找贺小花同志核实过,血型也和川田美幸子夫妇的相符。川田美幸子是被逼无奈从军的,现在她是日本一个反战同盟的负责人……
不知守岛老人这历经风霜的满脸沟壑里掩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
我们离开时,春江留在了岛上,他想劝老人跟他离开小岛。他说,只要老人愿意,他情愿给老人养老,并答应把两位烈士的墓也一块迁走。后来听说,春江的努力没有成功。
离开小岛前,我们要求老人带我们去了那两位烈士的墓前。我们想,有守岛老人在这儿陪伴他们,他们一定不会寂寞的。又一想,守岛老人不在了以后呢?
我们这些身在军营或曾在军旅的人,一个个缓缓举起了右手,久久没有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