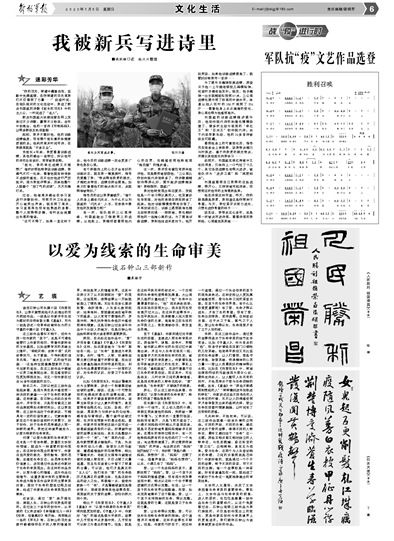读完石钟山的长篇小说《向爱而生》,让我不禁想起他不久前推出的另外两部作品:一部是以作家早年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散文集《重逢》,另外一部是讲述一位革命前辈终生为烈士守墓的中篇小说《守墓人》。
这三部作品看似不相干,但作为同一位作家的“孩子”,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作家的烙印,带着作家特有的文学基因。比如故事背后的英雄主义情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式的叙事技巧,长于素描、干净利落的语言风格,“滴水见太阳”式的细节刻画……这些特征就像雕塑家的刀法、书法家的笔法,在这三部作品中都被一以贯之地展现出来,而且感觉较以往更加挥洒自如,足见一位作家在过去30多年间练就的功力。
除此之外,之所以把这三部作品连起来看,是因为我在其中感受到一种共同的意蕴——关于生命的审美意蕴。这种意蕴,在石钟山此前众多作品中,并非没有,只是没有像这三部作品展现得如此鲜明突出。这让我觉得,这三部作品对于作家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意义。它意味着作家在这个年龄阶段和时代背景下,对于创作、对于生命的思考都进入到一种新的境界。我把这种境界概括为,以爱为线索的生命审美。
何谓“以爱为线索的生命审美”?这本是一个哲学命题,放置在文学创作领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观念。在这种创作观念的影响下,作家自觉用爱的眼光、爱的触角、爱的思维,去感受生命百态,去思考生命的价值意义,进而通过作品表达作家对于生命的审美观念。在这样的作品当中,以爱为核心的情感,成为作品勾连情节、设置矛盾冲突的主要线索;生命成为隐含在作品背后的主要审美对象;爱对于生命的塑造过程及结果,构成了作家表达生命审美观念的载体。
应该说,通过“爱”来开掘生活、展现人生,石钟山的优势是明显的。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创作中,从早期的《父亲进城》《幸福像花儿一样》《母亲,活着真好》等开始,再到晚近一些的《军礼》等,石钟山的目光多数时候都徜徉在不同人物的情感世界,特别是军人的情感世界。这其中自然少不了从不同侧面对“爱”的观照。这些观照,使得故事从一开始就被染上了暖色调。无论生活多么复杂纷繁、曲折艰难,人生多么跌宕起伏、结果难料,爱就像流淌在地平线下的温泉,让人常常于激情热烈、矛盾冲突、挣扎抗争等生命经历中感受到绵长暖意。这是石钟山过去多年作品中十分动人的地方,也是石钟山作品始终拥有较大读者群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此前这些作品中,“爱”并没有像《重逢》《守墓人》《向爱而生》这样,如此紧密地与“生命”联结在一起,让“生命”直接成为审美对象。此时,情节、人物、环境等故事元素已然被置于次要位置,而由这些元素叠加融合后所传递的观念,则成为作品最重要的部分——对爱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对爱之于生命的认识。
比如《向爱而生》。作品以警察宋杰为主要线索,讲述一个制毒集团被侦破的故事。按说,这是一个可想而知的充满曲折悬念的故事构架。然而,结果并不像读者期待的那样。故事主体没多少让人意外的情节,甚至显得有些程式化。比如,卧底、药厂伪装、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的勾结等,都有些似曾相识。整个案件侦破过程,也并没有想象中的悬念迭起。显然,作家并没有想把这部小说写成一部悬疑探案类型的小说。所谓案件侦破的故事主体结构,其实只是整部小说的一个“壳”。“壳”里的内容,才是作家想要重点铺陈的。于是,失去母亲的幼儿小满、珍爱女儿的马教授、遭遇感情挫折的马晓雯等,相比于警察宋杰、老板王文强等与案情侦破的关键人物而言,不仅占据了大量笔墨,而且也在读者心中留下了较重的分量。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公”,他们有关“爱”的生命经历才是真正的故事主体,也是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再极端一点,假使作家换一个“壳”,不是警察破案而是潜伏暗斗、草根逆袭等其他故事类型,里面装的关于爱的故事,恐怕仍然大同小异。
相比于《向爱而生》,《守墓人》《重逢》中“以爱为线索的生命审美”倾向就更加明显。《守墓人》中,作家对“他”的描述是极为平淡的。故事中几乎没有半点矛盾冲突,几乎没有可以称之为悬念的情节。但是,就是在这样平淡无奇的叙述中,一个沉甸甸的生命寄托显得愈加厚重。大山里那几座烈士墓构成了“他”生命中分量最重的部分。“他”因此奔赴战场,因此在战后回到大山,因此至死也没有离开过大山。在这样的故事当中,生活平淡如水,而承载着人间大爱和生命价值的元素,高高耸立在生活的水平面之上,愈发清晰夺目,愈发直击灵魂。
至于《重逢》,作家则通过对早期生活的回望,直接进入到生命审美状态。那些弹弓、球鞋、战争片、军帽等,被作家从碎片化的生活记忆中剥离出来,并且与人生命运连在一起,充盈着岁月的光泽和生命的色彩,被赋予了丰富的审美意义。作家看似是在平淡地讲述自己的生活史,事实上早已经“拿起画笔”,在进行着基于自己生命的审美活动。而这其中,无论是战友、儿时伙伴之间的真挚情感,还是因此带来的人物命运起伏,“爱”始终是“生命审美”不曾绕开的线索。
那么,仅从这三部作品来看,作家通过“以爱为线索的生命审美”,给我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呢?
在长篇小说《向爱而生》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正上幼儿园的小满,亲眼见到来接他的妈妈,突然被一辆卡车撞飞。父亲宋杰一直敷衍他说,妈妈没有离开,只是飞到天堂去了。小满不知妈妈何时能从天堂里回来,就是日思夜盼地希望妈妈能够早日回来。在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有一天他给妈妈原有的手机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电话竟然接通了。那边竟然传来“妈妈”的声音。电话那边的“妈妈”刚开始怔了一下,当听到“我是小满……妈妈,我想你”后,“妈妈” 沉默了一会,湿着声音说:“妈妈也想你”。从此,小满又有了“妈妈”。
爱,让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重新找到了“妈妈”。爱,让一个孩子关于妈妈的情感逻辑,没有因为突发事故而中断,相反以这样一个合乎事理逻辑的方式得以完整。生活,让一个孩子的生命世界出现裂缝,而爱,如此完美地填补了这个裂缝。爱,让一个孩子本将残缺的生命,得以完整。这就是爱的力量,这就是爱之于生命的力量。
爱,让生命得以完整;爱,可以弥补生活给生命带来的残缺。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这样的故事也不鲜见。但是,作家的巧妙在于,把这样一个道理,通过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的视角来表达。这种安排让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爱与生命之间的紧密关联。在孩子的生命世界里,有什么比母爱更重要呢?有了爱,生命才得以成长,才有了生的希望;没有了爱,生命注定暗淡,或将凋零。这种密切关联,近乎水之于鱼,氧气之于人类。爱让生命得以生,生命因爱才有了立于人世的根。
当然,在这三部作品中,通过爱的故事传递关于生命审美的细节还非常多。比如《守墓人》,作为老兵的“他”,终身守护曾经在自家门口牺牲的几位英雄。他简单平淡但又无比坚定的生命故事,让人们看到,爱是守护崇高、珍爱英雄、传承精神的心灵力量——爱让人类最美好的精神得以永续。比如在《向爱而生》中,深谙法律和刑侦的马教授因为爱女心切,最终走向杀人,让人慨叹人生无常的同时,不免思考关于爱与生命悲悯的命题。还有,《重逢》中“那些不断遇到和想起的人”“深深镌刻进年轮轨迹的存在”,作家讲述这些不同角色的人生命运的时候,无不让人仿佛感受到岁月珍珠散发出来的温润光泽,爱让生命在回望时暖意融融,让时间有了沉甸甸的质感。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说,这三部作品就像一部多乐章的交响曲。不同的声部,不同的乐章,都在讲述关于爱的故事,演绎不同的人物命运,最终又都归结于“生命”这一主题。那些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人物命运,与色彩斑斓、姿态纷呈的“爱之花”,交相辉映,甚至互为因果。爱与生命,这两个与人生密切相关的命题,之间的关联到底是怎样的?作家所做的,就是通过一个个不同的故事,给予不同的回答,写下不同的注脚。每一个故事即是一种答案。所有答案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作家对于生命这一高度抽象概念的审美结果。
文学的人文属性,决定了文学承担着生命审美的重要使命。事实上,文学作品与生命审美的距离、进入的层次,也往往是衡量一部作品生命力的重要标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石钟山连续三部作品为我们展现的,不仅是创作观念上的变化,更是作家在创作与审美境界上的更高追求。我们期待石钟山为读者奉献更多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