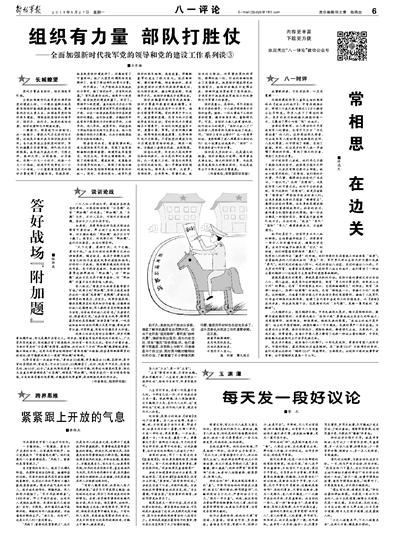圣人曰“三立”,其一为“立言”。
“立言”情有所不敢,力有所未能。若如苏辙所云,“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段好议论”,则作为目标可,终身实践亦可。
人生百行百业,总有一行是属于自己的。干好自己这一行,方不白来这世上走一遭。说来惭愧,本人体脑俱弱,力不能提刀上马,忝为文人之列,这“发好议论”之说,自非为他人所言,理应专为文人而发。
吃白食,是现今的说法,《诗经》里叫尸位素餐。后人加以发挥,更进一解,说:不但有益于世为不素,即益于世,如果日间不作一善事,不增一学问,不发一好议论,便是素餐。一日如是,虚度一日;一年如是,虚度一年。素餐孰大于是?按照这个说法,为文的没有写出好东西,就等于吃白食。以此来衡量,这行当白吃白喝的人应该不少吧?
南宋的洪迈,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容斋随笔》。他本身在朝廷作官,任翰林学士。有一天他侍奉在皇帝身边,孝宗忽然问他:“近来恍惚见甚斋随笔?”
洪迈不知道皇帝这话什么意思,紧张地回答:“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没有什么价值。”皇帝说:“很有些好议论。”洪迈这才放下心来,并连忙起谢。后来他把这件事郑重地记在书里,说:“书生遭遇,可谓至荣。”受到皇帝的垂青,洪迈写得更加卖力了。
随笔里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史实的考订和评论。孝宗皇帝如此说法,可见他是认真地读了这书,而且眼光也是不错的,因为后世跟他同样看法的人还有不少。史称他是南渡后最有作为的皇帝,想必是从书里吸取了不少治理的经验。
明清之际,有几个文人我是又爱又怕的。爱的是他们胆子大、敢说话,能言人所未言;怕的是他们每每戳到你的痛处,使你一会儿脊骨透凉,一会儿双面发烫,冷热间作,如犯疟疾。
先说这袁中郎。他议论的泼辣,乃是独树一帜的。他评价庄子和荀子,“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他讥讽当时那些记几个烂熟故事、用几个现成字眼的人是“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他批评那些“剽窃影响”之作,如老妇人涂脂抹粉,愈显其丑,徒增人厌。
好议论的“好”,首先体现在情感上的“真”。中郎写信给他的好朋友江盈科,说自己“越行诸记,描写得甚好”,大概玩笑话占十之七,严肃的话占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他说,把这些作品拿给那些作假事假文的人看,他们会极其怨愤怒怪,如果给兄弟您看,你肯定会笑倒无疑的。
他为江盈科作传,说他的文章“有俚语,无套语。俚语虽可笑,多存韵致。套语虽无可笑,觉彼心中,烂肠三斗,未易可去”。中郎说,文人可以有俚语,但不能有套语。而有些文人专用套话作不痛不痒文章,读来犹如嚼渣,更无一篇可存于世。
好议论的“好”,还表现为意思上的“新”。人家这么说,你也跟着这么说,那叫拾人牙唾,不叫好议论。而许多好议论,恰恰是平常语。
明代的李贽,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和思想家。他论文道:“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奇,莫过于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暖、饥能饱,又何其奇也!”所以他说,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这能说是新奇吗?在他们看来,文章议论新奇,原无一定格式,发人所不能发,一一从胸中流出的东西,才是真新奇。而当时的一些人,有一种“新奇套子”,表面看似新奇,实际上是陈腐,尤为可厌恶之甚。
读好的文章议论,常常觉得“此中有人”,有人的情感、人的爱憎,字字欲飞、纸纸欲立,而不是如僵尸一般,死气满纸。我学写一点东西,恪守一点:尽量多写点事实,多写点故事,尽可能地少发点空论,少说点套话。理想固然崇高,达到实属不易,不被讥为“嚼渣”亦幸矣。
好议论并不限于文字。就是寻常说话,也可以少一些家长里短、米盐琐屑,多一点识人论事、社情民俗;少一些官职升降、钱财出入,多一点人民疾苦、百姓痛痒。
清代的汪钝翁,与某宗伯议论多不合。一日,他与严白云论诗,对白云说:“您在宗伯门下最久,你认为他说的什么话为确切不移的谛论?”白云举出他说的一句话:“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钝翁听了,不觉爽然自失,才不得不佩服他。
“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穷腹。”好议论最怕挦扯割裂。尤其是一些以文为业的人,出口全是道理,细想全无道理,尽是一面之理。正的反说,反的正说;今日这么说,明日又那么说;今日见些子道理,明日又见些子道理,这是最误人的。
“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这两个方面,都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