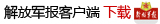再过半个多月,来自黑龙江绥化望奎县的王立生就要去广东湛江拾掇土地,为冬种做准备。
从2014年起,每年秋天都有一批东北农民跨越4000公里,如大雁南飞般迁徙至温暖南国,在湛江遂溪广袤的红土地上播种马铃薯,期待来年春天的丰收。
4年过去,最初在钗仔村开辟的500亩试验田,如今已扩大到1.3万亩,遍布草潭、北坡、杨柑等几个乡镇。
这场创造性的“北薯南种”,不仅跨越空间,让来自寒地黑土的马铃薯在南国红土地上生根发芽;也“穿越”时间,让东北农民享受到一年两茬收获的喜悦;更带来双赢,盘活了遂溪的闲置土地,为当地农民带来就业机会,增加收入。

望奎县龙薯联社在遂溪县草潭镇钗仔村租下4800多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张锋锋 摄
从猫冬到冬种:“要真做成了,我们也能一年种两茬”
就在几年前,对望奎县大多数农民而言,“冬种”还是个陌生的词。
东北冬季寒冷漫长,农作物一年只能长一茬。在绥化,十月金秋,气温便已低至零下,之后便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农民们早已习惯了春种、夏忙、秋收和“猫冬”——热炕头上打打牌、唠唠嗑,躲避漫漫寒冬。
别说普通农民,就连望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文,也是到2012年才了解“冬种”的概念。
这位自称“生长在屯子、工作在屯子,一辈子都是屯子人”的乡镇女干部,那年46岁,刚刚就任望奎县东郊镇党委书记。
在当年一次马铃薯产销对接会上,李亚文得知,在广东、福建一些地方,冬天也能种马铃薯,而且收购价几乎是黑龙江的两倍。
“冬天也能种地啊,我心想这事太好了,一定要给我们镇老百姓找点事干。要真做成了,我们不也能一年种两茬嘛。”李亚文对南都记者说。
李亚文所在的东郊镇是个马铃薯种植大镇,早在1998年就在全国注册了第一例薯类商标“黄麻子”。
李亚文告诉南都记者,与很多东北农民一样,东郊镇的农民一年有近半时间闲着,“一般人均5、6亩地,收获了就自给自足,外出打工的少。10月,农民把地里收拾完,天就开始下雨。到11月,农民就彻底没事干了,搁家‘猫冬’。我就想给他们找点事做,别闲着。”
有了“北薯南种”的想法,李亚文“歘歘就走了”。她先去福建学习冬种经验,又折回广东寻找适宜种植马铃薯的土地——拿着地图一路向南,惠东、开平、徐闻、海安、遂溪,那些之前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她都用双脚踩了一遍。

李亚文在遂溪县草潭镇钗仔村的土地上。
吃过闭门羹,甚至被当成上访户撵出来;遭遇过台风,车被掀翻还摔了一身泥;苦哈哈跑一路,无功而返更是常事。“那时才40多岁,也是年轻啊,有闯劲,不知道害怕。”李亚文笑着感慨。
一找就是三年。
“我不可能整年往外跑,大多是利用我们春种前的一个多月去找,有时一年跑两趟。”李亚文说,马铃薯的生长对气温、气候、土壤等都有严格要求,因此她每次去找地都要带回约20斤土样,“在不同地块上取几个点采点土,到家我就搁盆里试种一下,再送一部分去检测土壤酸碱度。”
李亚文说,她找过的地方差不多70%的土壤都适合种马铃薯,限制条件主要还是温度和气候。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要查询当地历史天气情况,和当地老百姓了解情况。“适宜马铃薯生长的温度是18-25度,像湛江40年都没有霜冻,就敢放心种,广州附近就不行,一有霜马铃薯就全军覆没了。”
最终,李亚文来到雷州半岛,将目光锁定在遂溪县草潭镇,那里地处北部湾北岸,气候温暖湿润,土地沙化属红砂土,特别适宜种植马铃薯。此外,当地农民大多以渔业为生,闲置农田辽阔而平坦,更适宜规模化种植和大型农机作业。
“就搁这儿了!”在当地镇干部的协助下,李亚文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土地。
2014年9月,李亚文带领家乡的几个种植户,去草潭镇钗仔村试种500亩马铃薯。2015年,大规模的“北薯南种”正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