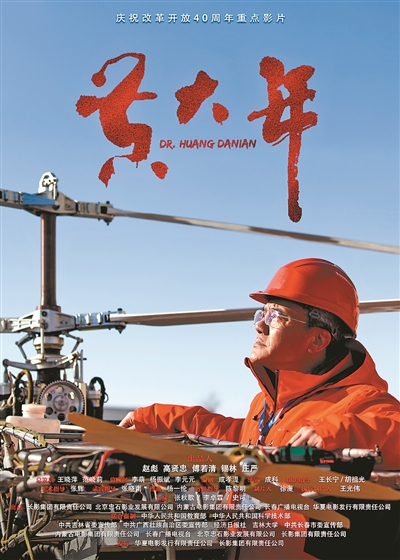看了《黄大年》这部电影,心里回响着很多情感和很多格言,其中最强烈的就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以及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影片开始是以黄大年妻子的叙述视角展开倒叙,中间有第三人称全知叙事、黄大年自述与回忆、学生刘江的内心独白和追忆等多视角穿插,结合顺叙、插叙等多种方式,显示出很强的文学性。
看完整部影片不难发现,整体节奏毫不拖沓,也没有任何思想包袱,显得十分干脆利落。黄大年的亮相真的是别出心裁:茫茫大洋,都是美国人的舰队战机,整幅荧幕只有黄大年这一个中国元素。而且面对美国将军的咄咄逼人,黄大年不急不躁地戳穿美国人的谎言,甚是坦荡磊落。之后情节一转,经过一番紧张的追踪锁定了失联的亚瑟号。整个过程节奏紧凑,寥寥数笔就勾勒出黄大年的性格特征:有理有节、直率真实、自信专业、充满正义感。
黄大年的形象不免让人联想到钱学森、邓稼先。事实上,黄大年也是大师。影片中,吉林大学校长对黄大年表明他何以是东北地区首位引进的“千人计划”专家时如是说:“你的归国能使外国舰队在中国的海岸线后撤一百多海里。”国内学术界对黄大年价值的认识,恰好呼应了当年美国军方对钱学森的评价:走到哪里都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具有国际性和国际视野,他们的价值举世瞩目,他们也是深度“融入世界”的尖端人才,所以由他们说出“人类命运”话题的时候,才会丝毫没有虚假的成分,理直气壮。
这样的呼应,既有新时代的新气息,也有一股很强烈的历史感。当钱学森、邓稼先的义无反顾连接起今天黄大年、南仁东的义无反顾,历史虚无主义被现实击得粉碎。这种导向无疑是编剧成孝湜的精心谋划,这从他大胆虚构刘胜文这个角色即可见一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给黄大年量身打造一个“前史”来解释主人公人世命运的发展逻辑。如果讲述历史的时候能够摒弃“断裂论”,采取唯物史观和缓泰然地将当下与历史进行细密的勾连,又何尝不是一种大写的自信?20世纪70年代中期,17岁的黄大年进入广西地质队,结识了影片中的挚友刘胜文。而刘胜文的侧面刻画,正是黄大年坚定专业选择与回国建设的重要动因。1977年恢复高考,黄大年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精神旗帜的“七七级大学生”。1992年,黄大年获得珍贵的公派出国名额,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深造。因此在影片中黄大年动情地说:“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其实何止改革开放,他一生的经历——从地质队时期、参加高考到出国留学再到新时代不断改善的科研环境——都是我们国家历史的塑造。与钱学森、邓稼先一代大师相比,黄大年这一代真正算是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尖端科学家。站在这样的角度审视历史,黄大年回国的决心就显得充沛饱满。
黄大年海外游学、任教及科研多年,身上的“世界性”已经浸入骨髓:流利的英语交流、和谐的人际关系(告别画面中出现了多种肤色)、优雅的绅士做派、娴熟的大提琴技能以及默默支持街边的流浪歌手。然而,他又是“最中国的”:比如开头搜索亚瑟号体现出的刚正不阿和诚实守信;比如多次怀念挚友刘胜文和感恩改革开放时体现出的仗义疏财与知恩图报;比如对家人的深切关心与含蓄的关怀方式;比如遭受误会时体现出的“人不知而不愠”的温和儒雅;比如在他课堂板书中出现的“白居易”,表明他希望将中华文明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起传授给学生。“中国内核”与“世界性”看似矛盾,其实有内在深刻的必然联系。当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必然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多元融合要以多元共生为根基,彼此平等,互相尊重,才会形成“世界性”共识与命运共同体。同时,多元共生也需要不迷失自我,才能更好地沟通对话,提供自己独特的文化经验,这就是“中国内核”的重要意义。因此,兼具“中国内核”与“世界性”的黄大年在离开西方科研团队的伙伴时,回身对送行的“世界人民代表”儒雅温和地绽放微笑,在此刻东西之间的沟壑被填平,壁垒被拆除,中国和西方现代化强国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彼此充满敬意与温情的合作关系。
作为一位80后编剧,成孝湜在前辈身后无疑充满创新的热情。比如对正面和负面的处理,成孝湜认为“我们写善的时候,从善良中看到危机感;写恶的时候,我们需要以悲悯的情怀去反思这种邪恶的根源。”黄大年初回国内,面对本土部分学者效率低下、利益心和得失心重、小团体派系意识普遍、团队协作能力缺乏、人际关系微妙等状况,一度心灰意冷。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令人感慨,影片涉及的学术怪相不可谓不真实。面对现实,黄大年重振旗鼓,坦露心迹,以身作则,以“倒下了就地掩埋”的先锋姿态逐渐改善了科研生态,创造出一项项重大成果。影片中,黄大年的性格并不只是儒雅温和这一学者标配,而是呈现出更立体的人物形象:急怒时也会凶猛踢门,见到老友也会克制不住想去撸串,心情压抑时也会驾驶跑车雪地漂移;驾驶员和院长都不同意他带病加班时,他竟然威胁说要跳车;让人笑着默念“男人至死是少年,赤心不改真英雄”,弥留之际叮嘱学生穿着自己在利兹大学博士答辩穿的西装去参加答辩,认为那是一套“吉利服”,尖端学者瞬间转变为慈爱父亲;朋友劝他不要因为爱国而毁了自己的大师之路,他则笃定地宣称自己已经是大师了。成孝湜洞悉青年一代的心理结构和期待,一方面强烈反对艺术被资本绑架、被市场左右,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与观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积极交流,正是这样的身份和诉求,决定了《黄大年》是一部新时代的主旋律作品。可以说,这部作品也应当归入他所说的近年“主旋律的美学升级”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