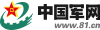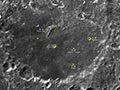家乡绥中有个军用机场,有一年“八一”节,学校组织我们去机场看飞行,我吃惊地看着银色的飞机腾空而起,又从天而降,看见飞行员穿着飞行衣、戴着飞行帽,从飞机上下来,高大而神气,心里又崇拜又羡慕。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在机场旁边一站许久,看飞机、看飞行员跳伞,似乎就在那时,飞上蓝天的梦想逐渐在心里扎下了根。
1983年6月,我顺利通过招飞考试,成为保定航校1700多名飞行学员中的一员。报到后,航校要组织入校摸底考试,成绩不合格就会被退学。那段时间,我整天捧书苦读,把争强好胜的劲头全部用到了学习上,成绩逐渐名列前茅。
在军校的最初几个月,从精神到身体,整天都是紧绷着的。一开始不适应,但是过了这一段,这种严格的纪律观念就渗入到每天的言行举止,养成了一种习惯,让人感到遵守纪律规范成了很自然的事,这也影响到了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包括以后成了战斗机飞行员和航天员,虽然在某些方面要求更加严格,但我并没有感到有多大困难。
正是青年时期那些艰苦的训练、严格的纪律、身体和精神上的锻炼,培养了我、影响了我、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军人做事追求极致,强调执行力,要做到胆大心细、准确认真,尤其作为飞行员、航天员,任何细小的误差和失误,都有可能影响到任务的完成、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军中无小事,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决定生死。
在军旅生活那些紧张、痛苦和单调之中,也有一种特别的阳刚与明亮的美感,尽管学习训练非常紧张、艰苦和严格,但并不排斥我们的爱好和个性,反而有助于培养我们在发展兴趣爱好上的毅力。
我在航校期间,喜欢上了唱歌、弹吉他,成了文艺骨干,后来到航天员大队,又成了航天员乐队的黑管乐手,还经常当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这些都要感谢军校对我的培养。

前排右二为杨利伟。
1984年夏天,我和几十个同学被转到新疆的空军第八航校去学飞小飞机,也就是战斗机。八航校训练任务重、淘汰压力大,我们那一期近70名同学,到四年后毕业时,只飞出来十几个人。大家时刻面临压力,都希望第一批放单飞,避免停飞和淘汰。大部分课目,我都做到了第一批放单飞,但是在抗过载和高速翻滚两个课目上遇到了障碍,为了克服它,我在正常训练之外给自己“加餐”——左手捏右耳、右手捏左耳,原地打圈,锻炼前庭功能。
1985年,我顺利完成了初教6和歼教5单飞训练。随着飞行次数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娴熟,就有意尝试一些动作,玩一些花样。初教机一般只能飞到4、5千米,我和同学们有时故意在空中较量,看谁还能飞得再高一些。向上爬升中有时忘了时间,等意识到按正常飞行已经不能准时回到机场,而不能准时就算不合格,情急之下我们就驾机向下猛扎,在规定时间内返回。飞低空时,我们会故意飞得很低,有时从50米的低空快速掠过,巨大的轰鸣和强烈的气流,把地面的羊群惊得四散奔逃。
飞行员大多都有这样的顽皮故事,它是飞行快乐的一种释放,源自对自己和战机的熟知,也是在充分掌控的前提下,对危险的边界的体验与品味。
1987年夏天,我的军校生涯结束了。毕业离校前,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120多块钱。同学们每人都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骄傲地穿去逛街,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要的就是这种“拉风”的效果啊!我们听见了,还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但最后大家还是憋不住劲,一路笑着回了航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