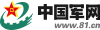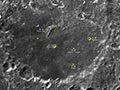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围绕“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的主题报道要求,为了更好展示70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航天事件和成就背后的故事,中国航天报社策划了“共和国航天往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系列主题报道,从8月16日起在《中国航天报》及新媒体上陆续推出。
1955年,二战的硝烟散去,冷战阴云密布,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
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临时修改了发言稿,提出“会议应该求同存异”。会议开创了亚非国家独立自主讨论和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先例,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
此时,中国航天事业也在秘密筹建之中,一个叫做“国防部五院”的特殊机构应运而生,中国人也要搞自己的导弹、火箭、卫星。
在暗流涌动的1955年向前瞭望,当建设新中国的集结号吹响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科技星火,都纷纷扑向九州华夏,汇聚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
1955,在路上
1955年,时任大连工学院动力工程教研室主任的王希季副教授,如往常一样把头发梳成三七开,换上一身新式中山装,准备和妻子聂秀芳一起去上海,从大连工学院(后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调入交通大学(后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建国初期的大连工学院人才济济,光学家王大珩任应用物理系系主任,电子学家毕德显任电机系和电信系的系主任,造船专家杨槱任造船系主任。
王希季在这里如鱼得水,自己先后编写了《锅炉学》《涡轮机》《铸工》等教材,开设锅炉学、蒸汽透平、涡轮机、船舶汽轮机等课程,又用了一年时间基本掌握俄语,与同事杨长骙、殷开泰一起翻译苏联教材《船舶汽轮机》。学院建新校舍,他还主动承揽了一批建筑的全套取暖系统的设计工作。
工作刚满五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王希季所在的大连工学院的船舶动力系并入交通大学。不久后,王希季在上海遇到了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同学杨南生。
他俩都曾是系足球队的主力,王希季是行动敏捷的右前锋,杨南生是眼准手稳的守门员。
海外学成归国后,王希季去了大连工学院,杨南生到钱学森创办的力学所工作。
十几年后的老同学重聚,两人一起为新中国研制液体探空火箭,向太空冲刺。

1953年,王希季与聂秀芳在大连寓所合影
1955年,年轻的梁思礼博士带上短袖收拾好行囊,准备去越南出差,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成年后的梁思礼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先生的影子。
这是梁思礼到邮电部工作的第六个年头了。他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所建发射台、架设天线,给新中国建立国际广播电台。这次出差是新中国为兄弟国家做援建,帮越南建设“越南之声”广播电台。
梁思礼他们仅用两三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胡志明主席为他们颁发了勋章和奖状。
在越南没有多做停留,梁思礼便匆匆回国了。他最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姑娘赵菁(原名麦秀琼),他们在研究所的周末舞会上相遇,一起跳了一支圆舞曲。姑娘的眉眼温柔,裙裾翻飞、舞步轻盈。
谈起心爱的姑娘,梁思礼充满了爱意:“她聪颖、细心,使我在任何困境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微笑,拥有一颗快乐的心。”
从越南回来不久,梁思礼参与制订新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梁思礼基于邮电部的工作经验,对无线电、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设想,还大胆地参与了新技术部分的讨论——《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
在讨论会上,梁思礼和钱学森意见一致,在发展飞机还是发展导弹的问题上,他俩都认为:“航空发动机很难搞,需要较强的工业基础,飞机在短时间内是很难研制成功的,而搞导弹能很快看到效果。”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这次规划决定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梁思礼人生的发展方向。
不久后,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钱学森任院长,梁思礼任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

梁思礼和赵菁
昆明,西南联大与王希季
如果问,天才少年家道中落是什么体验?
十岁的王希季会盯着小说头也不抬,“不知道。”
按成绩算,王希季可以免试进入省立中学,但是家里生意不景气,又赶上1931年发大水,父亲的货在武汉全部泡了汤,一家十几口的开销没有着落。没钱交学费,表哥建议王希季读昆华工校的附属中学,将来升入工校既能学一门技术,“饥荒三年,饿不死手艺人”。
所以王希季又去考了一次试,以第一名的姿态走上了学技术的路。
初中,王希季爱看小说,三年时间把学校图书馆的小说看了个遍;踢足球,在初中部足球队是当仁不让的前锋;游泳也是出了名的“浪里白条”,一鼓作气游上以一两千米不成问题。
高一,王希季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考上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机械系。
西南联大人才济济,王希季年纪小,职业学校的课才学了一小半,数学课连代数都没学完,就开始学微积分。
最让王希季“耿耿于怀”的是,机械学大师刘仙洲先生让他吃了第一个零蛋。在一次测验中,刘仙洲先生给出题目,要求计算准确到小数点以下三位数。“小天才”王希季举起计算尺刷刷刷就算完了。
结果一看成绩,零蛋。因为计算结果的小数点下三位是根据计算尺估算的。
今日,王希季对刘仙洲的教诲还牢记在心:“刘先生给了我零分,让我终身受益。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我考试中的小数点下三位就是缺陷。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零。”
挑战与乐趣同在,西南联大注重对人的素质的培养,当时物理学家杨振宁、翻译家许渊冲和王希季是一届的,大家一起上过国文课。
在大一的课堂上,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魏建功讲《狂人日记》。
在许渊冲的记忆中,钱锺书先生给他上课时才28岁,戴一副黑色大眼镜,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还常常身穿一套咖啡色西装,有时也会换上一身藏青色礼服。在1939年3月31日给他们上第一课的时候,钱锺书一口流利的英语,要他们学习标准的伦敦音。
当时许渊冲在天祥中学教英文,在给聂秀芳的班级讲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秀芳说:“如果希季敢做罗密欧,我就敢做朱丽叶。”十几年后,月老的红线果真把王希季和聂秀芳牵到了一起。
杨振宁说,“我们3个人分别在文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并不太熟。那时候我们就有很大分别,我和王希季活动范围小,许渊冲就不一样,他很活跃。西南联大当时的漂亮女孩儿,他都追过!”
后来,文学院的许渊冲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理学院的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工学院的王希季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国立西南联大校门
天津,南开中学与梁思礼
如果问,出生名门、幼年丧父是什么体验?
少年梁思礼会站在饮冰室门口,想起已经过世的父亲梁启超,说“爹爹太爱我了,我也太爱他了。”
1929年梁启超离世,他一生多数时间都在为国运奔波,去世时没留下多少银钱,最珍贵的遗产是天津租界的两栋楼和一整套《饮冰室合集》。
梁家两栋楼,旧楼是普通洋房连着一个后楼,全家和常住的亲友都住在这里;新楼是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的两层半小楼,一层是梁启超写作、藏书、接待客人的场所,靠北的三间房是相通的,屋里的书柜从地面立到房顶,新楼还有一个名字——饮冰室。
梁思礼在饮冰室附近的培植小学读完书,1935年考上了南开中学。时任校长的张伯苓先生定下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校长很重视体育,学校组建了网球、篮球、足球、排球等运动队,当时南开的体育团体有182个。
回忆高中生活,梁思礼说:“在南开中学,我们接受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我们不是书呆子,而是兴趣广泛,经常从事体育锻炼和各式各样社会活动的全面发展的热血青年。”
七七事变后,南开中学在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中一直很活跃,被日寇认定为“造成反日情绪与反日活动的中心”。1937年7月28日,日军对南开学校进行野蛮轰炸,梁思礼站在海河东岸,看着母校被日军飞机俯冲投弹、狂轰滥炸,被夷为平地。
学校炸没了,梁思礼和同学们被吸纳到耀华中学读书。
中国近代力学大师钱伟长是他的物理老师,在讲完物理课后,钱伟长会留下部分进步同学,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音乐老师张肖虎教授乐理之余,还组织各项音乐活动,指挥学生们合唱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正如他的父亲梁启超所言,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后来,国文老师何其芳去《新华日报》任副社长,音乐老师张肖虎创作出《苏武》《木兰从军》等一系列博采中西的音乐作品,同窗好友陆孝颐成为一名地下党帮助留美学生回国,梁思礼成为火箭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 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梁思礼(前)和五哥梁思达(左一)等在天津饮冰室院门前
“我要为新中国造发电厂”
1942年王希季联大毕业,选择去21兵工厂工作。自己不能上战场,他说,“到兵工厂工作是为了打日本,雪国耻”。在兵工厂干到第三年,抗日战争胜利了。
第三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兵工厂迁去南京时王希季递上辞呈,内战烽火又起,他不愿自己生产的炮火对准自己的同胞。
不做军工,王希季选择去昆明耀龙电力公司发电厂。当时云南的电力资源匮乏,王希季回忆,“现在计量电力值是千瓦,在当时是马力,也就是那么多电能相当于一匹马。”
大理没有像样的工业,只能用汽车引擎带动发动机发电,照明电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都很少见,大部分都是靠煤油灯照明,买不起煤油的人家只能用菜籽油。
怀着一腔热血,王希季准备大展拳脚,可是去了才知道,这个“大发电厂”实在小得可怜,以他现在的才学,想设计建设一个大型动力厂,要学得东西还有太多。
罢了罢了,既然苍山洱海、风花雪月中找不到建设中国的答案,那就走出国门,师夷长技,来实现自己建设电厂的梦想。
1948年,王希季全力以赴争取留学机会,最终考上了。他辞别刚订婚的女朋友聂秀芳,到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读书,攻读燃料及动力专业硕士学位,为建设发电厂积蓄力量。
按照研究生院的教学安排,学生不仅需要修完学分,还需要每隔一日就到学校所在地的热力发电厂工作8小时,结合所学专业积累工作经验。每天最晚一节课3点结束,王希季就到电厂去实习直到半夜,不去工厂就到图书馆看书。
弗吉尼亚州位于北纬36°至39°,到了11月开始刮寒风,12月开始飘雪花,这是春城昆明看不到的景色。
王希季在学校每天凌晨一点睡下,早上7点起床,完成一天的课业后,到发电厂先从打扫卫生开始做起。从锅炉工、加水工、电工、主机工、组长,一直干到领班,最后可以独立全面地负责电厂8小时的工作。

1948年,王希季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生宿舍
“我要给老百姓办工厂”
梁思礼高中毕业了,看着他长大的丁懋英大夫和耀华中学陈晋卿校长,帮他写了两封推荐信,附上高中三年的成绩单,他申请到美国嘉尔顿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母亲王桂荃变卖家中值钱的物件,东拼西凑出400美金,给梁思礼买了张去往美国的船票,临行前把剩余的100多美金塞给梁思礼,嘱咐道:“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记住祖国还在蒙难,学成了一定要回来报效国家。”
抵达美国不久,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战争中断了梁思礼与国内的一切联系,没有通信、没有钱,17岁的少年孤身一人踏上征程。
全额奖学金只能解决食宿,穷学生梁思礼课余时间到学校食堂洗盘子、当服务员,没有钱参加周末聚会,就去游泳池打发周末,后来在普渡大学时还入选校摔跤队,成为全队最轻量级的选手。
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梁思礼跟着同学罗伯特·肖搭上顺风车,跑到纽约州的水牛城,在罐头厂做工,饿的时候就吃流水线上的豌豆。
假期同学们都回家了,他打开学校唱片图书馆的大门,躺在草地上听古典音乐。
梁思礼回忆起这段经历,说:“被逼是消极的,但也有积极意义。人在被逼无奈时可以激发出自己的巨大潜能,培养自己不服输的硬气,促使人竭尽所能想办法,克服困难。”
1943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租借法案,对盟国给予援助,在美国留学的盟国学生每月可得津贴75美元。梁思礼在获得津贴后放弃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转入美国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两年后,梁思礼从普渡大学毕业。
普渡大学的工程专业非常有名,从这毕业的还有半导体器件物理专家王守武、“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梁思礼当时打算回国后办几个砖瓦厂、洋钉厂、小电扇发动机厂,走实业救国的路子。
他写信给好友陆孝颐:“对我自身,幸福很容易解决,一口饭,拉洋车也可赚得出来。如果人生之乐只在于自己养活一个家,实在无多大味道,尤其我的机会是这样好,我则更应对没有机会的老百姓多负些责任。”

1949 年,梁思礼(左一)与留美学生参加CSCA小组会
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
1949年,王希季与潘良儒合作完成一篇题为《分散态煤粒的燃烧研究》,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同年,梁思礼提交博士论文《超高速离心机》,获得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
国内传来消息,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最终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
9月23日,医学专家严仁英、王光超,中国日报社副总编陈辉,25岁的梁思礼博士和五姐梁思懿一家四口,从旧金山出发,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次年3月,王希季自觉已经有能力为新中国建设大型发电厂,当即辞别教授、同学,放弃近在咫尺的博士学位,也踏上了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有人问起王希季,为什么不继续留美读博,他答:“我出去读书时国内还没统一,回来时已经统一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从我出生时起,国家就一直在混乱中,要么是军阀,军阀之间还打内战,要么是日本鬼子侵略,国家支离破碎。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对个人来说,统一就需要建设,统一意味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有可能会实现。”
归途中,王希季遇到了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地质学家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和数学家华罗庚,华罗庚写下《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归国后,梁思礼和王希季先后被调入国防部五院。这里的工作有“三不准”:不准向无关人员,包括家属和亲友暴露自己的工作性质;不准暴露机关的住址,对外联系只能用信箱代号;不准随便与外国人接触。
一度,这些航天人的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与梁思礼一同留学归来的老朋友陈辉说:“他回国后好像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
梁思礼的女儿梁红回忆:“从小到大,我对父亲的工作一无所知,直到我也进入航天系统工作,才知道一点点。后来父亲年纪大了,我去做口述资料的整理,才明白当年我父亲那一代人多么伟大。”
从美国旧金山回国直线距离接近一万公里。当时,王希季、梁思礼在海上足足漂了一个月,才从美洲大陆回到华夏九洲。
轮船靠岸,一个在“沉默”中书写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风雨不改飘扬了70载。我们怀念的西南联大,也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了。
载着科学家们飘洋过海归来建设祖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45年前已经报废了。
那些耀眼的名字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就像腾空的火箭,从勃发耀目的冲天火焰,逐渐化作天边一颗闪烁的星辰。
想起1956年钱学森组建团队,集聚各路才俊,中国航天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梁思礼仿佛预见到了今天,他生前给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青年授课时,引用萧伯纳的名言作结:
“人生并不是一只短短的蜡烛,而是我们暂时的拿在手中的一只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后一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