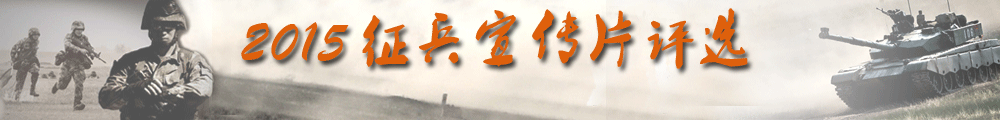从香港撤退的最后一个航班
1941年12月8日8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他们还大规模轰炸了中航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客运飞机。
中航停在启德机场共有八架飞机,其中的五架(25号、26号DC—2,寇蒂斯1、4、5号)在轰炸中化为灰烬,仅存两架DC—2、一架DC—3,但也是千疮百孔。
日机突袭香港过后一溜烟飞走,启德机场一片混乱。唯一的办法是尽快往大陆撤退,先把国民政府政要撤走,再把中航剩余物资转运到内地。
中航经理命令陈文宽,立刻驾驶已经受伤的DC—2往南雄撤运物资,回来马上飞重庆撤运政府要员和公司眷属。撤退在12月9日晚上7点开始,三架还能起飞的飞机无一例外全部受损。坐在驾驶舱中,冷风从弹孔里不断灌入。陈文宽当天飞了两班香港—南雄往返航班。从重庆返回南雄后,陈文宽疲倦得瘫坐在座位上。
12月11日,陈文宽驾机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后,中航公司命令陈文宽再次飞返香港,并一定要在午夜之前返回重庆。陈文宽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不能出任何闪失。
接近黄昏时分,陈文宽把DC—2降落在启德机场,不一会儿,舱内装满了各种货物,问题是,还有27人准备登机,而DC—2最多能载14人,这么多货物,又这么多人,很多乘客注意到,年轻的机长轻轻皱起眉头……
午夜时分,机翼上标注着CNAC的DC—2在启德机场终于抬起头,向着重庆方向飞去。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和诸多国军高级将领也在航班上。
几个小时后,香港沦陷。这是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启德机场的最后一个航班,飞行员是陈文宽。
降落密支那并创造世界纪录
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印度俨然成了抗战中中国的大后方,中国航空公司开辟的重庆—加尔各答航线,是中国外部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和国民政府要员出访和学者国际交流的唯一通道。
5月7日,陈文宽从加尔各答回到重庆,以为能休一个班后再飞,但公司命令几乎和他降落珊瑚坝机场同时抵达:明天(8日)再飞一个重庆—昆明—加尔各答往返。
5月8日早晨9点,DC—3缓缓向起飞线滑去。滑行中,陈文宽接到公司总部发来的电报命令,在昆明降落加油后,务必临时降落一次密支那机场(缅甸境内),以便接出中航驻守机场场站人员和抢运出所有航材。电报中还特地说明,据留守人员来电告知,今晨,密支那已经听到日本人枪声,所以请陈文宽争取时间,尽快飞行。
DC—3滑到起飞线,陈文宽正要推满油门迅速起飞,塔台突然传来指令:暂缓起飞,美国大使馆有重要客人前来搭乘此机。
足有30分钟,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到起飞线,几个美国军人匆匆上了DC—3,陈文宽迅速升空,航向对准昆明疾速飞行,他必须把刚才等待的时间在空中抢回来。
DC—3刚刚进入云南境内,巫家坝机场又发来紧急电报,日军正在攻击巫家坝,陈文宽这架DC—3必须马上就近降落。陈文宽将DC—3临时降落在昭通。一个小时后,巫家坝机场空袭警报解除,得手后的日军飞机扬长而去,陈文宽驾驶着DC—3降落在四周还不时冒着青烟的巫家坝机场。
加油、下客、上客,手续交接等诸多事项办完后,陈文宽迅速让DC—3再次升空,他不敢再有丝毫耽搁,密支那那里的人员和器材时刻都让他心中悬块石头。
在重庆迟到的那几位美国军人对飞行谙熟,从昆明起飞后不久,他们察觉到陈文宽的航向并非是飞往加尔各答,而是向着有日本人的地方飞。他们顿时紧张起来,为首一人闯进机舱质询陈文宽:为什么改变航向?
陈文宽告诉对方,遵本公司命令,要临时降落密支那,接出那里的人员,否则,他们有被日军俘虏的可能。美国人让陈文宽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陈文宽微笑着答应:一定!
美国人的紧张不是没有道理,质询陈文宽的那位就是刚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的杜立特中校。杜立特担心,如果这名中国飞行员把自己和同伴送给日本人做礼物,他将得到一笔巨额收入,日本人将得到美国大量机密情报。
DC—3降落密支那,奇怪的是,航材和公司人员并不在这。而日军已到密支那城南,正向机场开来。
逃难的缅甸人把DC—3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往里钻。陈文宽从驾驶舱里隐约能看见日本人的先头部队。按照“先妇孺,后男人”的顺序,陈文宽和杜立特跳下飞机,把最后几个人强塞入机舱,困难地关上舱门,发动引擎。
傍晚,DC—3在沉重的咆哮中,重重地砸落到加尔各答机场跑道上。
后来成为四星上将的杜立特在日记中写道:飞机落地后,在后舱内一共钻出72人。其实,将军不知道,副驾驶后来在例行检查中在行李舱内又发现酣然入睡的6名缅甸人。
只能载运28名乘客的DC—3竟然载运78人,顿时轰动了全世界。太多的人记住了陈文宽这个中国名字。
这是密支那机场的最后一个航班。
飞越驼峰新航线
密支那被占领之后,为保证正在抵抗中的国民政府外援通道畅通,中航公司和美军印中联队被迫在人类尚无法飞越的喜马拉雅、横断大山地带开辟另一条航线,即驼峰航线。
但驼峰航线让中航和美军人员和飞机损失惊人,未雨绸缪,必须再闯出一条新路。
新航线起点定为重庆。机长—陈文宽,副驾驶—潘国定,随机报务员—华祝,全是“中航”精英。按委员长、最高军事委员会、交通部的指示航线要必经四点:重庆、迪化(今乌鲁木齐)、白沙瓦、卡拉奇,绕开缅甸,直接进入印度(当时,印度、巴基斯坦尚未分离)。
1942年7月18日清晨,成都凤凰山机场,国民政府航委会主任毛邦初和另一空军军官在此登机监督本次飞行。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陈文宽驾驶着C—53昂首蓝天,向着中国北部纵深与浩瀚荒漠,向着人迹罕至的边疆飞去。兰州只是这次航程的第一站,小停、加油后,C—53一口气飞到迪化,飞行航线基本上是沿着古丝绸之路前行。陈文宽知道,再飞就是伊犁,接着是越出国门,而前面就是横贯东西的天山山脉和喜马拉雅并行的喀喇昆仑山山脉,此前,这个地区从来都没有人飞过。
第二天8点多,天刚放亮,陈文宽带领机组就起飞了。此时地面是盛夏,5000米高度温度却是零下十几摄氏度,陈文宽和副驾驶潘国定操纵飞机,报务员华祝抓紧在飞出国境前发报。
没飞多久,白雪覆盖着的天山挡住去路。C—53升限高度是5000米左右,天山山脉犹如拦路虎挡在前面,无法跨越,好在天气好,无云,竟然看见一个“豁口”。陈文宽没有丝毫犹豫,奔着豁口就飞了过去。
阳光遮挡住了绵绵峡谷,沿着九曲回肠的叶尔羌河,C—53如同一只寻找巢穴的大鸟,在低沉的鸣叫中缓缓前行。C—53闯进明铁盖山谷,山谷如此之大,两侧遮天蔽日,上下不断有大块白色的云团扑面而来,C—53顺着还可以依稀见到山谷的走势而行。山谷太长,C—53飞了十分钟都没有出去。突然,一团浓密的乌云拦腰截断去路,在山谷中钻云,就是找死;转弯退出,速度快、转弯半径大,稍不留意还是会粉身碎骨。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陈文宽迅速放下起落架,副驾驶潘国定迅速打开15度襟翼,紧接着,陈文宽又压了45度坡度,C—53速度马上减了下来,这样,用了很小半径转弯,又转了回来。
转出来,再次爬高。幸好是空载,C—53吃力地吼叫着费力爬到6000米,还是在峡谷中,但却是在两个云层中间,透过这两层云,可以看到前面的山峰。没有犹豫,陈文宽顺势推杆,C—53高声吼叫着,转眼飞到喀喇昆仑山另一侧。过了这道“坎”,就没什么阻碍了,接着是白沙瓦、德里、卡拉奇、加尔各答。
后来得知,这条航线,美军第10航空队也飞过一次。路线也几乎和陈文宽机组这次飞的如出一辙,只是反着来—先从白沙瓦出境,但到喀喇昆仑山口时,遇上相当恶劣的天气,没过去,又折了回来。
陈文宽机组开辟这条驼峰新航线,是驼峰新航线第一个航班也是最后一个航班。虽然后来并没有启用,但陈文宽和他的机组用生命和胆略闯出新通道。
陈文宽一生热爱飞机、飞行,眷恋祖国。
对话陈文宽:“我答应了就要飞过去,哪怕摔掉”
记录好过美国飞行员
时代周报:我查了很多资料,得知上世纪30年代,你就执飞重庆—成都航线了。
陈文宽:是的,当年上海首航北京,我是副驾驶。上海至汉口我也飞过,重庆飞成都航班,我是机长。
时代周报:抗战爆发后,有一次急于到前线的中国军人抢占航班,用枪逼迫美国飞行员飞行,最后导致美国机长全面罢工,去了香港,只有你一人留了下来,默默飞行,是因为你是中国人吗?
陈文宽:美国飞行员作出的选择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美国政府还未向日本宣战。你也知道,一旦宣战后,飞越驼峰航线如此艰险,牺牲如此之大。我之所以在那次罢工时选择留下,是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大难当头,大家能做一点,就分担一点,或许国家就会减轻一点苦难。
时代周报:从1942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飞越驼峰航线无论是单机载运量还是飞行损失,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一直保持最好的飞行纪录。比如,美军人员飞越驼峰航线50次就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可以回国休假。而同期的中航公司中国飞行员飞越驼峰航线最高纪录是接近1000次,你执飞客运航班至少也有300次,而且这些纪录多数情况下是在飞机超载和机组人员不足情况下完成的,你如何做到的?
陈文宽: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飞越驼峰航线,无论是谁,不管飞行品质是优秀还是平庸,每个人遇到的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和日本飞机拦截的机会均等,这话是对的。之所以中航飞机单机运载量比美军要大而损失率却比美军要低,经验,是飞行经验帮了大忙。美军从遥远的地方过来,对驼峰航线上的地形和气候都不太熟悉,很多时候,是他们的指挥官硬逼着飞中国运物资的。当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没有外援物资进来,国家就不能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