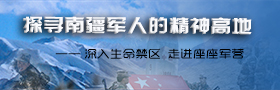侠与匪咫尺之遥
虽然有“盗亦有道”的理论,但是土匪往往不愿戴盗的帽子,而愿打侠的旗号。
侠与盗的源头不是一回事。关于侠的定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气力也。”《韩非子•五蠹》说:“其带剑者(即游侠),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政府)之禁”。简单地说,侠是一种志趣相投、无视法律、靠武力横行的团伙。韩非把儒和侠列在“五蠹”之中,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主张“离法者罪”,“犯禁者诛”。
似乎是为了给侠正名,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游侠列传》。他满腔热情地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其意为:虽然游侠的言行不合主流,但言必信,行必果,答应了的事肯定去做,为解“士”之厄困,把生死置之度外,事后不图回报,不夸耀自己的能力和道德,所以有足以获得美誉之处。请注意,司马迁说的是为解“士”(区别于农工商的士人,包括做官不做官的读书人)之厄困,而非解民之厄困。也就是说,侠不是普度众生的菩萨,不是什么人遇到困难都会帮的,而是为特定主子卖命的。《游侠列传》中的侠都是为有知遇之恩的主子行侠的,其中三个牺牲了性命。
有意思的是,后世史家修史都以《史记》为蓝本,却唯独没把《游侠列传》继续作下来。紧接着《史记》修《汉书》的班固不但不为游侠立传,而且公开说司马迁笔下的游侠郭解之辈“不入于道德”。然而,正史不言侠并没有影响侠文化的传播,正如鲁迅所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且不说,只说清末民初出现了一股侠义小说热,如《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三侠五义》)等层出不穷。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电影业也加入进来,根据小说《奇侠英雄传》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大红大紫,成为票房冠军,以致连续拍了18部续集。1928年至1931年上海的50家电影公司一共拍了500部影片,其中武侠片就有250部,占了一半。值得深思的是,在民初,与空前的侠文化热同时发生的是空前的匪患高潮。侠文化没有孵出侠,却孵出一群群侠之流的匪。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故凡侠义小说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中国小说史略》之《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对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鲁迅颇不以为然,指出:“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侠的本质是奴,按此标准,鲁迅把强盗归入“侠之流”。他以《水浒》为例说:“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