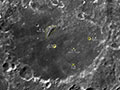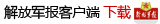“二月河”一浑而东
△二月河
二月河是一条在军队“过滤”过10年的水,携带着深深的战士烙印——守时守信,能咬牙、能忍受、能吃苦,知道前线在哪里,一个时期只做一件事……
我的生命前期似乎与“8”字有不解之缘。我1948年3岁,随母亲渡过黄河,从此由“山西人”变成河南人。1958年母亲调到南阳,我又随母亲来此地变成纯粹的“南阳人”。1968年我从军,由一个满身中学生味的“知识青年”变成了青年军人。1978年呢?
1978年是我命运的重要转捩年。比前头几个“8”那种生活小转折不知重要多少倍。那一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南阳。对我作出返回家乡的决定,父母亲都是不太赞同的。他们的理由是:“你在部队干得好好的,领导也很器重你。地方上乱哄哄的,派性也很厉害,你回来干吗?”他们作如是观,但我也有我很实际的想法:1978年我已33岁,这个年纪现时有人已经干到正团级了,就是当时,野战军里干到正营甚至副团的也大有人在,而我还只是个连里的副指导员。部队封闭在大山里,是个独立团的架子,团长政委虽然对我好,但他们本身也就这么大的“力度”,干下去还能怎样?再看,部队图书馆的书大致我已读尽,再想学点新东西,也是难以为继。于是,在政委跟前软磨硬泡,终于“跟了第二批”,转业了。
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我已经在部队嗅出浓烈的“真理标准讨论”气息,从山沟里走出后,更觉得铺天盖地的都是新的信息。改革开放的呼声已经走出地平线,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浪潮越来越高。多少年后回想这段历史,我有一种“从山里到城里”的感觉,思想得到了全新的武装。因为有了较大的图书阅读范围,原有的历史知识也迅速膨胀起来。这就萌生了“创作”的冲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叫“从量变到质变”。我在部队10年读书10年积累,是量变。一旦环境改变,气候适宜,我要由一个军人向文人转型了,我要把自己阅世读史及观情的体味变成文字,告诉读者,这是质变。
其实,写作与读书是又相关又有分割的两件事。读书是你个人的事,朗诵、轻读、默念、浏览、掩卷而思……都是你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写作是传播理念,思维沟通心灵信息,有高低、粗细、文野、深浅种种分别,与读书水准密不可分。但写作是“告诉”,是“社会的事”。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创作理念的问题。写什么都是可以的,但写什么都是履行社会责任和你的人格责任,都要拥有堂堂正正的社会责任心。
比如我要写《康熙大帝》,我的责任编辑就告诉我:“一定要把康熙的阴险毒辣虚伪和残忍写足。”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理念,康熙是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不阴险谁阴险?他不虚伪谁虚伪?但我认为康熙是伟大的,大帝大帝,你就必须把他的“大”字写足。
这一理念的确立,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是不可能的。康熙他是封建君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剥削贫苦农民、维护地主特权……他都是有的,你歌颂他,你是什么阶级立场?
但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可以使我有胆量作另一维思考:康熙,3次亲征准噶尔,6次南巡,停止修长城,采取民族敦睦政策,测绘全国土地绘制《皇舆全览图》,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解决台湾问题,这都是他的民族大义大节,史籍皆斑斑可考,当然是应该歌颂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这个标准,我当然可以肯定他并把他作为正面人物塑造。这一种思维,把时间推移到1978年前,整个社会恐怕都会说你是“阶级立场有问题”。
我在领悟1978年,定出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创作原则:只要是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出贡献的;只要是在发展当时生产力,为改善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作出贡献的;只要是在当时为科技文化文明教育作出过贡献的,我都肯定他,赞扬他。如与3条“只要”相反,我就鞭挞他,藐视他。历史上的实践,同样是检验历史人事的唯一标准——这当然是我在不断的学习和创作中慢慢领会和体悟到的。
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尚在部队。在这之前,我有9年多时间在军队中生活,不但学知识,学理论,学做人,而且学会思想,学会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二月河是一条在军队“过滤”过10年的水,携带着深深的战士烙印——守时守信,能咬牙、能忍受、能吃苦,知道前线在哪里,一个时期只做一件事……待到冲锋号吹起,我就冲了。当我走进军队时,还不过是个懵懂毛头小伙子,当我从里边走出来时,我已是个拥有社会责任心的大人了!
这冲锋号,在1978年响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响起,响亮了全中国,也响出了一条河。我的“二月河”的含义,就是改革的春风化冰,咆哮的春水一浑而东的那种壮丽景观。
(原文刊登在2008年02月28日解放军报)